小熊英二、王升远、李远江:个体记忆、历史罪责与家族史书写
小熊英二的著作这些年在中国读书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译介。但事实上,我对小熊最初的了解并非始于他的个人著述,而是他与上野千鹤子二人对鹤见俊辅先生的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作为访谈者,小熊的位置感、问题提起的视角以及推进的深度,是非对战后日本思想史脉络有深刻把握者所难为的。
接下来,他的另一本书《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也被译介到国内。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倾听者的姿态,带着社会历史学家的感觉将父亲一生经历予以历史化和学理化,让我们透过一位普通日本人的生命史看到了某种带着温度和个人实感的20世纪日本史。这两本书在中国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同时,小熊也很关注中国国内李远江等推动的家族史调查。一些机缘巧合之下,我们三人相互交换了一些关于家族史研究、历史记忆问题等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之看法。作为抛砖者,很开心地看到了那些不成熟的提问所引带出的金玉之言,更期待三地书中的这些文字能让我们在对个体生命和家族足迹的叩问与追寻中成为更真诚、更理性的倾听者、对话者和书写者。
——王升远
王升远:极端年代的“全历史”写作
小熊老师、李老师:
初秋时节,向二位老师纸上问好。《新京报·书评周刊》邀请我们以通信的形式来讨论一下家族史写作和历史记忆的问题。这几年,李老师推动的家族史访谈、调查和小熊老师的《活着回来的男人》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想或许正好可以借此机会面向读者朋友们展开说说。我个人这些年在处理战争和战败初期作家日记以及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等相关问题,也会涉及一些战争记录、战争记忆和书写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困惑或者感想也想借机向二位求教。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20世纪”(short20century)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战争与革命,“短20世纪”也因此被他称作“极端的年代”。在李老师策划推动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中,对于当代中学生而言,祖辈在极端年代的记忆是绕不过去的。而小熊老师的父亲谦二先生也经历了战争,并在西伯利亚做过苦力。两者要处理的对象与问题中,都绕不开“极端语境下的人”及其判断、选择与行动这些自带痛感的问题、难题。个人史、家族史也因民族国家历史的风云变幻而受到剧烈的冲击与波及。历史从个人、家庭、家族流淌过后留下的痕迹成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日本历史乃至全球史的重要“证言”,我想或许可以将其视作被遮蔽的“另一半历史”。事实上,在道德教训可能只对个人有用的同时,政治教训却必须由群体一起来汲取;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也是培养个体人格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事实上需要很多个谦二,需要很多个父辈、祖辈的记忆叙述,并形成一种召唤力量,以呈现、拯救被宏大叙事收编、挤压、遮蔽的“另一半历史”,这是“全历史”(Totalhistory)写作的要求,是当下的我们对历史不容回避的责任,也是今天我们来讨论历史记忆相关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还是坚信个人的历史、家庭、家族的历史有着不容替代、不容代言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作者:王升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
与强调个人、家庭、家族的意义不容遮蔽相应的是,其责任也不容推卸。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一些峥嵘岁月、极端年代中,一些人会以集体、国家之名作恶,事后复又躲在宏大叙事背后洗脱、逃避个人责任,战败初期不少日本知识人便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制度的问题、国家恶的问题自然不容忽视,但是若只将问题归结为组织、集体、国家、民族甚至意识形态因素等结构性因素,那么责任问题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架空并走向虚无,人之为人的尊严、理性之光也将随之无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犹大和总督的追究都是不可偏废的。因为即便同在一个极端的年代,面对相同、近似的状况,每个人的判断、选择和因应策略也大有不同。就我个人近年来关注战争时期日本知识人精神史相关议题而言,大致情形就是这样的。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把战争与革命都视作一套化学意义的“反应装置”。对于日本文坛而言,战争成了一种无可选择,也几乎无法逃避的反应装置,他们被今人期许的道德、良知、价值、伦理、爱国心等等无不需要在此之下经受非常态的酷烈考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原形毕露”。
如果我们把战争视作加热装置——煤气灯,将战时的法西斯主义政治氛围比作氯气,以此来测试身处其间的日本文学家之“活泼性”。金属钠在不需要加热的状况下,遇到氯气就能与之发生反应,这就很像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文坛操盘手菊池宽,永井荷风就曾在其日记中痛骂菊池败坏文学、出版两界风气的恶行。而铁就不一样了,它与氯气之间在不加热时缓慢反应,而加热的情况下则会剧烈反应,这就像战时大部分文学家的境遇和抉择。当然,也有银这样的金属,不加热不反应,加热后缓慢反应,中野重治就属于此类作家。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中野便因时局的变化放弃了其一贯的立场,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而最可贵的是金,无论如何加热,它与氯气之间都不会发生反应,这就类似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志贺直哉等为数极少的几位疏离时局、战时保持缄默的文学家。这些年,我将关注点转到战后初期的文学与思想时,又会很关注日本作家战后的责任认知和自省,这也是千人千面。其中,不断否认、推卸责任者或者对此保持缄默者居多,但每当读到为数甚稀的对极端年代中之个人言行公开讨论和忏悔的文章,都让人心怀敬意,这意味着一个个体甚至是一个民族面对苦难的道德回望,面向未来,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
面对极端时代的个人抑或亲族的言论和行动是需要勇气的。小熊老师熟悉的日裔旅美学者桥本明子有本书叫《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作者发现战败后归国的日本老兵对过往自己在亚洲诸国的战争经历不愿重提。而作为家庭、家族中的大家长他所具有的身份权威,也使得家庭、家族成员不会主动谈论、轻易触碰其比较忌讳的过往。桥本认为两三代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双重壁垒”是导致战争记忆风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像小熊老师父子之间能够坦诚相见的案例并不多见。这就引出了战中派的“战争体验”与战后派的“战争经验”之间交叉、融通的限度问题。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作者:[美]桥本明子,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2月。
很想知道,小熊老师父子对话中,是否出现过父亲在情感上难以逾越、不愿触碰的痛苦过往,您在对话和这本书的写作中是如何处理的?在读《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时,小熊老师面对鹤见先生的提问是极为坦率、直逼死角的,但历史眼光逼视下的很多提问以及鹤见先生的回答都让人深受启发、深有触动。那么,在面对父亲进行交流、访谈并将其个人经验历史化的时候,父子的家庭伦理以及历史社会学者面对历史亲历者之间的学术伦理在写作中是如何交错和平衡的呢?
小熊老师的《活着回来的男人》给我最初的震撼是您所着意凸显父亲带着常识、常理的常人生活,在人性之常、生活日用之常中重新审视历史及物于个体后留下的印迹以及个体的回应,这是另一种与精英主义、精英叙事相对的历史观念。您强调父亲的选择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这里也流露出鲜明的“均值”意识。将对自己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父亲予以“一般化”处理,强调作为“均值”个体的普遍意义,便有力地破除了民族国家框架的强力绑架及其在有形无形中向人们输出的某些观念的羁绊。在全球化遭遇困境的今天,保持这种基于常人之常识、常理而形成的对他者的想象力、对遥远的哭声之共情心、同理心,是极为可贵、极为重要的。

《活着回来的男人》,作者:[日]小熊英二,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在某些情况下,鼓励面向父辈、祖辈的对话、交谈恐怕首先旨在恢复、接续抑或重建某种跨越代际的“联系”,而这种因家庭伦理而本应坚韧存在的情感联系实际上在“极端的年代”曾遭到破坏而断裂,我想这种现象很多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就我个人而言,自小时起,我就对自己家庭、家族的历史比较留心在意,但又发现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他们的回忆都是断片化的、有选择性的,更无法期待某种全景叙事了。细想起来,这里至少存在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祖父和父亲在面对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时,在心理层面自觉不自觉间是很难将我视作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对象的,他们会刻意回避了一些艰难痛苦的话题,时而还会带着某种“讲故事”甚至“寓教于讲述”的道德训诫意识选择性重构自己的记忆,跨代际的交谈会在不觉间发生奇妙的焦点转移。
同时,因为种种内在的、外在的原因,他们的讲述里面也存在不少记忆的讹误。这就带来了历史记忆、口述史的“文学化”问题。在做作家战争日记、战败日记的研究中,也会遇到文学化或者说“虚构”的问题。即便是日记文本,有时也只能视作某种日记文学,即便是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乘》也是如此。在处理日本作家战争日记和战败日记这类文本时,如何思考其中的真实性问题曾经长期困扰过我。后来我想,或许我们有必要区分“事实真实”和“情感真实”的关系。事实可以揉搓、变形甚至虚构,但是其中流淌的情感往往是真实的,无论是热爱还是憎恶,是敬畏还是轻蔑,情感层面的表达往往都会让人有“斯人诚不我欺”之感。当年中井英夫面对1970年代民间出现的美化自己战争记忆的风潮时,愤然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正是希图以战争中自己切肤之痛以及日记中对战争的憎恶来回应、矫正对战争历史的不当回顾。访谈中恐怕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虚”与“实”的问题。受访者对于一些具体的人事关系、时间、数字语焉不详或者出现记忆讹误,“实”的问题会谈得比较“虚”;但在状况、情境中自己的情绪、心境与判断、选择等这些相对“虚”的问题反倒会把握得比较“实”。总之,当我们带着赓续历史、传承记忆的期待,却极有可能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文学文本,这种文本有时又因其强烈的私人经验属性,很难通过证实抑或证伪。
而另一方面,从访谈者的角度而言,问题的设计中也无不受制、受限于其个人的性情趣味、知识结构、历史认识、家庭观念、关于同一事件的“后记忆”(Postmemory)以及当下语境对历史叙事或隐或显的影响和干预等问题,不同世代的人问题意识更会是千人千面。这会让我们的访谈文本充满着不确定性。而历史的真实也正存在于这闪烁、摇摆的不确定性之间。或许也无须带着历史学的眼光对其寄寓某种确定性的期待,因为谈论、写作家事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重新发现、认知自我并将自我相对化、历史化审视的操作,非此则无以谈成长,无以看清自我。李老师发起的家史、家族史中有一个自觉的意识,那就是对于青年一代而言,这是构建完善人格的重要基础,前辈的历史记忆对于后辈而言是某种面对社会的“间接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视角,这也启发我思考了另一问题。对于每个青少年而言,我们必须知道,祖辈、父辈的过往无形中已经作为某种你无法选择的前置约束条件,决定了你的生存条件、思维和行为模式等等。戏仿套用小熊老师采访鹤见俊辅先生时,鹤见的那个很有趣的提法——“方法以前的方法”。唯有把自己作为方法,才有可能更好地、真切地抵达原理与世界。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外乎是对二位老师学术工作的学习心得。期待得到二位的回应和批评。
王升远
2023年9月20日于上海
小熊英二:家族史研究
超越学术之外的意义
王老师、李老师:
读了二位老师的意见之后,我也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未能一一回应,希望二位能够从字里行间之中得到各自的答复。
在我看来,倾听并记录家族史这件事具有两大意义。第一、通过倾听民众那些无法用文字记录保存下来的生活史,去挖掘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事实,并呈现出与有文字记录者所不同的另外一种史观。二位老师肯定都很清楚历史研究中家族史所具有的这种学术意义。
家族史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它赋予民众以力量,让大家知道,在当权者眼中的无名之辈也有着自己的历史,从而树立起信心;让大家知道,不只有权威的书籍和记录,他们身边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通过倾听,让大家培养起自己创造历史、自己进行思考的能力;通过进行家族内的对话,培养起一种超越代际的想象力。这些虽称不上学术价值,却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进行家族史访谈时,以上两者密不可分的。不过,侧重点不同,倾听的方式和目标也会各有不同。
如果重点放在前者学术意义上的话,那么听到的事实是否属实,是否是史学界尚未掌握的有价值的新事实等方面则变得至关重要。听者需要具有能够冷静鉴别说话者所说内容是否属实的能力和业务知识。此外,他们还需要掌握如何从学术层面对所听到的事实进行定位的相关知识与理论储备。倾听的方法也必须将重点放在如何去发掘事实之上。

小熊英二,日本庆应义墅大学教授。
然而,不同的学科,其学术意义也千差万别。在人类学或民俗学中,有时倾听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引出讲述者的世界观,而非判断其所说是否属实。聆听街头巷尾的故事,它是否属实其实意义并不大。此外,在社会学中则更注重讲述者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即使其所讲述的内容并非新的史实,不过以讲述者社会地位的视角将他们的话语进行学术定位,这也是一种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视角。然而,虽然与历史学有所不同,但在强调学术意义,要求听者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及切实可行的方法等方面,则是相通的。
除此之外,比起其学术意义,如果更注重如何带给民众以力量的话,那么家族史的实施方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之下,通过家族史的倾听与被倾听,民众能够从中得到一定成长,那其学术意义便已无关轻重了。退一步讲,只要两代人能够进行对话,其实已经是一大收获了。这种情况下,学术知识和方法不再重要,话语的学术意义也可有可无。
所以我认为,必须将这两种意义加以明确的区分,方能进行系统性的讨论。重视学术意义,深化家族史相应的学术方法与理论,这条道路固然重要。但是,倘若重视民众自身成长的话,那么即使访谈后的学术效果差强人意也无大碍;倘若深化家族史学术意义的话,那么培养起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则变得至关重要;而倘若将家族史作为一种运动加以思考的话,那么或许会存在另外一种观点。
即便如此,在厘清二者区别的基础之上,还是存在着重要的一点,即与模板化叙事之间的距离感。
人类是不可能讲述所谓的事实的。我们无法做到将365天24小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在一小时之内全部讲述出来。如果非说不可的话,那么词汇贫乏之人往往诉诸模板化叙事。常见的苦难经历、电视中老掉牙的故事桥段、对年轻人的训诫等故事套路随处可见。米歇尔·福柯将这种模板化叙事对人类话语的规范称为一种“economy(经济学)”。我们在讲述时为了能够简化自己的经历,在听话时为了简化对方的话语,一种模板化的叙事便有了其用武之地。
然而,对于前面提到的两种意义而言,模板化叙事都是负面的。被压缩成一个已有的模板化叙事,那些相对而言不甚重要的体验或记忆,必会遭到模式的碾压而被抹杀。如此一来,我们或许便再也听不到那些一直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新史实,也听不到那些与文字记载所不同的观点了。更何况,仅去讲述那些模板化了的故事,既无法提高讲述者的水平,也无法锻炼听话者的思考能力。当得知听到的只不过模板化叙事的话,听话者自然提不起兴趣,也无法形成一种家族内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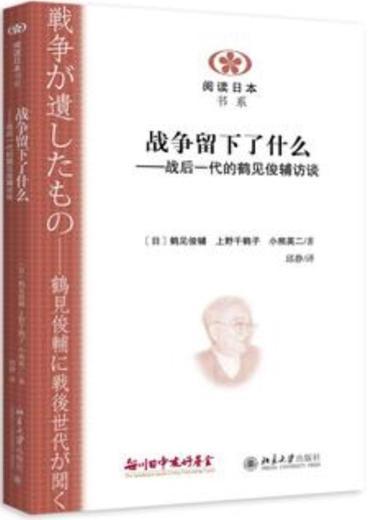
《战争都留下了什么》,作者:[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因此,我们该如何与模板化的叙事保持距离,对于这两种意义而言都很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并不存在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可供讲述者和听者使用的万能办法,那这其实也成了一种模式了。不过,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以下几招十分受用:
一是询问具体的事情,比如与其问“您当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不如问“您当时早上几点起床?吃的是什么?坐什么上班?上班都做些什么?”一天24小时,每小时的行动模式、吃什么、穿什么、见什么人,这些都可以问。如此一来,所说的话便不再抽象,对于逃离模板化叙事的惯性无疑是一种很好用的方法。
另外,最好询问他们当时的感受,而不是去询问意见。与其问“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不如去问“经历过这些之后,你的心情如何?”这里我举个例子,比如我问父亲在听到日本战败时是什么感觉,而并没有询问他对战争是怎么看的。父亲的回答是,在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他大约沮丧了20分钟,但随即又转悲为喜,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能活着回家了。这是与“日本人战败了都感到失望”,抑或是“日本人从战争解放出来都感到高兴”这种模板化叙事所截然不同的视角。与这两种模板化叙事相比,它可能更为接近史实。
此外,在倾听家族史的时候,访谈和被访的时机也很重要。我开始访问父亲正是母亲罹患住院的时候,没想到这倒成为了一个契机。当时,在一起去医院探望母亲的车里,父亲跟我谈了很多关于远方亲戚的事情,一个劲儿告诉我家里还有哪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听着听着,我也觉得“这些也挺有意思”。加之,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家,我每个周末都会过去看他,也没什么可聊的。事已至此,那干脆对他进行访谈吧。当时,林英一正好来找我商量研究的事情,我就拉上他一起了。没想到父亲的记忆比我想象的要清楚得多,他也很感兴趣,我便不停地追问。然后心想,这些都可以写本书了。就这样,通过访谈,不仅使父子关系变得更好了,书问世后父亲也很高兴。不过,他之所以开心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出名了,而仅仅是因为我把对父亲的访谈以书的形式流传了下来,我很喜欢父亲这种谦虚而又淳朴的性格。
如上所示,我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二位的问题。鄙人粗浅的作答,相信二位能够从中获取到有用的信息。
小熊英二
2023年9月22日于东京
李远江:家族史书写的内驱力
小熊老师、升远老师:
秋安!在北京到成都的旅途中看到二位的信,特别受教。
小熊老师对家族史的理论探讨及实践方法与我的经验非常契合,值得每一位想做家族史的人细细体会。
关于家族史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探讨,我认为还有一重特别的意义,那就是为家族史书写者提供强大的内驱力,同时为他们动员自己的家人参与或支持家族史书写提供合理性。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随时记录家族史的习惯。家族史写作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能坚持下来的人往往是少数。而家族史的意义和价值的挖掘和传播,能够极大地提升家族史书写的成功率。十多年前,我在动员中学生(后扩展至大学生和小学生)书写家族史的时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以及老师、家长能充分理解家族史的意义和价值。在我的家族史动员课程中,保守的评估,讲好第一课——《我们为什么要做家史》——这件事情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
到达成都的第二天,我趁着出差的间隙,去拜访了一位年逾九十的表姐。他的父亲是我的母校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第一中学第二任校长,是一位深刻影响了地方文化发展的教育家。而表姐本人是省内知名的煤炭工程师。2011年丈夫过世后,她曾经整理编印了一本记载夫妻二人六十年岁月的纪念文集,也帮丈夫一家编写了家族史。表姐从2019年就计划写自己的家族史,时隔4年仍未动笔。一方面她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她的家人对此并无兴趣。尤其让她痛心的是在弟弟去世前,她千叮万嘱让侄儿侄女一定要把弟弟的遗物,特别是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结果几个月后,侄儿侄女把父亲的房子卖了,遗物全部都烧毁了。表姐质问侄儿侄女,为何不听自己的建议,得到的回答是: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知道。时至今日,表姐仍痛心疾首,斥责侄儿侄女不仅没文化,更是不肖子孙。晚辈的无视让她觉得写家族史失去了价值,于是打算放弃。我和表姐聊了两个小时之后,表姐深受鼓舞,决定现在就动手书写自己的家族史。
关于家族史的意义和价值的讨论或许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苏轼在《题西林壁》中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家族史就像苏轼眼中的庐山一样,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综合体,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升远老师关注到“极端的年代”的记忆,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家族故事,我们可以看见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还历史以丰富多彩,复杂多元的面相。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家史故事,即使同样身处“极端的年代”,每个家庭或个人自身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的家族史依然是千人千面,而非模板化的故事。

《我们的家史》,李远江主编,出版社:鹭江出版社2015年1月。
升远老师还提到家族史的书写与承担历史责任的关系。我们观察到,青少年在倾听并书写家族史的时候,对历史的理解从抽象走向具体,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尽管绝大多数孩子关注的都是长辈的正面形象与积极的故事,却也有孩子能直面家族历史的黑暗面,深刻反思祖辈曾经的过错,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在我看来,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已经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深处,只要不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或美化家族长辈不堪的经历,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家族史书写者了。直面家族的负面历史,批判和反思家族传统是更高水平的家族史书写者才能实现的。
升远老师比较关注家族史的真实性,这也是历史学关注的焦点。在我看来,历史一旦发生就不可能百分百还原,但历史只要发生就会留下它的痕迹,这些痕迹就像大雁留下的影子,或投影于平静的湖水,或投影于汹涌的江河;或投影于猎人的眼睛,或投影于诗人的眼睛……同是一个本体的影子,但因投影的介质和方式不同,影子也各有不同。我们与其纠结于影子是不是真实的,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倒不如换个视角看每一个具体的影子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如是,我们或许更容易靠近历史的真实。
十多年前,我作为历史杂志记者前往山西考察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尽管当地文史学者言之凿凿,却无法解释为何明朝时期山西向外移民不过100多万,洪洞向外移民不过1万多人,而家谱中宣称来自大槐树的移民居然多达数亿人。毫无疑问,数亿人都来自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肯定不是历史事实。那么,我们讨论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其实不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老师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大槐树移民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明世宗推恩臣民祭始祖、立家庙,推动了民间追祭始祖和建置祠堂家庙的普遍化。由此,民间修谱,寻根溯源也逐渐普遍化。然而底层社会受教育程度很低,家族文献极为匮乏,口传历史又语焉不详,甚至真假难辨。一时间,北方地区出现了很多移民传说。这些移民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彼此竞争,大槐树传说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由此,原本坚持其他移民传说的家族就会成为乡村社会中的少数族群而遭受排挤。为了安顿当下的生活,他们明知是谎言也不得不选择接受大槐树移民传说。与此同时或稍后的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等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其形成与传播背后也都有现实社会的真实需求。
正如小熊老师所言,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通过家族史的倾听与被倾听,民众能够从中得到一定成长,那其学术意义便已无关轻重了。”因此,我们给参与家族史书写者的建议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绝不做没有历史依据的想象和虚构,这就是家族史书写的底线。在此底线之上,任何一种家族史的研究和写作都应该得到鼓励。
家族史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我想两位老师的理论探讨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敢于参与家族史的书写。也期待有更多学者参与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交流,共同助力大众参与家族史书写。
如今家族史书写方兴未艾,假以时日,当家史书写普及之后,彼此关联的家族历史汇聚起来,就会形成相互印证或相互批驳的关系,最终出现无影灯的效果。充足的家族史料会让历史学家更容易求取历史的真相,当然也会方便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
出差途中随想随写,不当之处,还望两位老师批评指正。
李远江
2023年9月24日于北京
作者/小熊英二、王升远、李远江
编辑/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