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孤独是作家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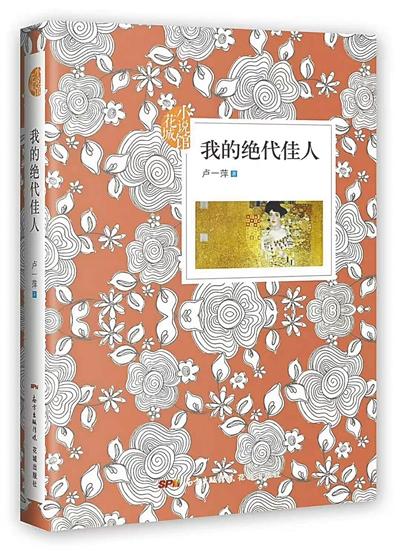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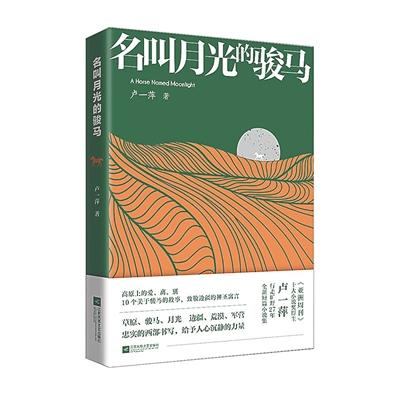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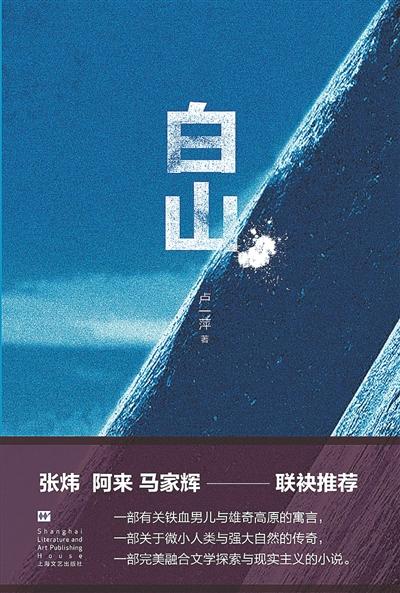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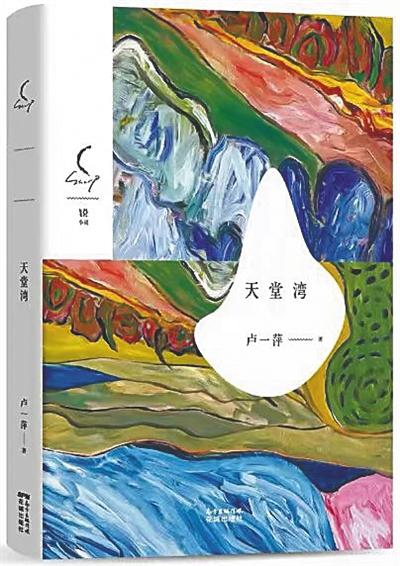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2022年10月,作家卢一萍推出短篇小说集《名叫月光的骏马》,登上媒体2022年11月严选的好书榜单,评委称之为文学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作品;2022年11月,《经典70后(上)(下)》出版,卢一萍与张楚、徐则臣等16名作家集结其中,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70后”作家的厚实功底。
卢一萍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作家。他在新疆生活了20年,行文中有高原的气息。他自称为“写作的游牧者”,是一个天生具有悲悯心的硬汉。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对卢一萍进行了专访。
一部神秘的高原心灵史
记者:先介绍一下这部《名叫月光的骏马》?
卢一萍:这部小说写了10个与骏马有关的故事,包括《名叫月光的骏马》《北京吉普》《夏巴孜归来》《七年前那场赛马》《克克吐鲁克》《银绳般的雪》等篇目,是我最心仪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这些小说既有见证了初恋美好如月光一样的小马驹,有陪着战士在雪域寻找丢失军马的雪青马,有与吉普车赛跑的大红马,还有知人性的老黑……从茫茫大漠到边疆哨所,我想用马来承载人物的豪迈与细腻,铁血与柔情,善良与澄澈,通过对置身草原、骏马、雪山、边疆、荒漠和大漠中各色人物的书写,能给予人心格外沉静的力量,并以此描摹出一部神秘悠远、雄浑瑰丽的西部高原心灵史,用这部小说集再次向西北边疆致敬。
记者:读完《名叫月光的骏马》后,我很长时间处于震撼中。集子里不同小说之间风格反差巨大,您是如何做到的?
卢一萍: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从我20年来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这个时间跨度决定了小说风格的不同。作家总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表达这个世界,所以,没法用一种风格,一种手法来写作。我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我是个写作的游牧者,所以我涉及的题材类型比较多,有乡村的、草原和高原的、荒漠的、也有城市的,有时,还有纯想象的,每一种题材类型有时得用与之相宜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写草原的小说语言相对要诗意一些,写荒漠使用的语言就会很凌厉,而写城市的语言现代感就会很强烈。也就是说,你如果用写乡村故事的语言去写草原,就不对劲,反之亦然。这是在写作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记者:这10篇小说都是写的高原,您是汉族人,但小说的修辞颇有高原上那些民族的味儿,感觉高原上的一切真的刻在您的骨髓里了?
卢一萍:我在新疆生活了20年,为了写作,有10年时间,我利用采访、采风的机会,以及做背包客,走遍了新疆、云南,去过西藏的大部分地方,我也在帕米尔高原生活过近四年。这些经历对我很重要。我体验了边地的生活,理解并喜欢少数民族朋友的生活方式。我要写他们的生活,要写民族地区的小说,就得懂他们的习俗、表达方式,理解他们的思想,行文中有他们的气息,我要融入其中并能与他们心灵相通。这是我必做的功课。
人性是作家永在探索的主题
记者:感觉您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乌有之地,但同时又有深刻的人心和人性问题蕴涵其中,比如《北京吉普》《夏巴孜归来》与《哈巴克达坂》等,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原也在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失去了许多,读完之后心里其实挺难受的,这种克制的写作需要有一定阅历和极强的功力,您在平时的写作中是否有意识地进行过训练?
卢一萍:我所创造的乌托邦其实都是实有之地。人心和人性是作家永在探索的主题。只要有人的地方,这二者都存在。一个地方也好,一个更广阔的地区也罢,其祸福因缘都受人心或人性的影响。但我们作为作家,即使是表达疼痛,也不会去大喊大叫,而会采取克制、隐忍的方式。作家的使命之一是承受并品味那种疼痛,然后写出来,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这的确需要一定的阅历,需要一些功力,这会随着作家自身的成长而逐渐具备。但有些东西是天生就有的,且不会泯灭,比如悲悯,比如良知。
记者:很多批评家在提到您的作品时,都提到了先锋性,您自己是如何理解并应用于作品中的?
卢一萍:我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先锋小说家,我也写过类似的小说,比如长篇《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那时我很注重语言、结构、形式感的探索。但后来,随着我对现实的理解深入了一些,走过的地方多了一些,就改变了对先锋的理解,它的含义变得越来越宽广。我觉得只要别人还没有写过的题材,你涉及了;没有触及过的现实,你去表达了;没有使用过的手法,你使用了,便是具有先锋性的。
记者:您之前曾说过想写历史上的西域36国,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开始动笔了吗?能否具体谈谈?
卢一萍:我是有过这个想法,我想依靠存留下来不多的关于36国的史料,选择十来个王国,写十来篇小说,虚构各个王国不同的灭亡原因,构成一部想象之书,希望以此向我喜欢的博尔赫斯致敬。
我多年前写过两篇,一篇叫《精绝》,另一篇是《姑墨上空的云》,都有颇浓的寓言味道。我得用富有荒漠气息(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早就湮没于滚滚流沙之下)的语言,又要有历史的韵味,内在的诗意,同时给每篇小说赋予现实意义,所以写作难度很大,很耗费心力,所以写完那两篇,就没有再写了。或许过上一段时间,我会继续写它。
最刻骨铭心的是别离
记者:您的作品有一种雄浑的坚硬感,而且辨识度很高,像日本电影里的那些硬汉。人们都说“文如其人”,您的人生里是否也有这些因素?说说您人生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部分?
卢一萍:我自认为,我算一个硬汉,这种形象不是银幕上的,也不是表演出来的,它更多地体现在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强大上,也就是你面对逆境时,是直面,还是屈服;在面对人生抉择时,是摇摆、退缩,还是果断、向前。你知道什么是你人生该做的事。因此,也可以说,硬汉更多的时候是被生活或理想逼出来的。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心由两个部分组成:柔情似水的部分和坚硬如铁的部分。当我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我柔情以待;当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假恶丑,我会变得刻薄、无情。
如果要说我人生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部分,有人认为是我在西部的壮游,我的确走了西部很多地方,但那最多只能算我人生难忘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的,我认为还是在面对爱、离、别时。爱情的到来与破碎,亲人和朋友的离世、战友的牺牲,不得不面临的一次次别离,都是我格外脆弱的时候。
记者:您的个人标签是“自语症患者”,有一种隔绝于世人之外的感觉,能否具体解读一下?
卢一萍:做一个“自语症患者”,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俗的日常生活。小说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颂歌,小说家是研究俗世生活的专家,要能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所以不能把自己隔绝于世人之外。
我也说过,小说家都是自语症患者,这也是小说家的一种状态。这跟小说这个体裁的特性有关,把现实中的人和事通过虚构,达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效果,这是小说家的职责。小说是通过虚构来达到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目的,所以,写出好小说的难度很大。一篇短篇小说有时也会耗费一个人一两个月时间,写一部中篇小说花费的时间会更长,有些长篇小说要写好几年,比如《红楼梦》,曹雪芹耗费一生也没有写完。所以独处书斋,俯首稿纸,就成了小说家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也正如我说过的,严格意义上讲,文学是孤独的产物,所以,一个作家承受孤独,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能力。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