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位诺奖女作家,写透了东亚女人的一生

历史上第一位亚洲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了。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19时,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韩国女作家韩江获此殊荣,成为历史上第6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韩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瑞典文学院给她的颁奖词是:“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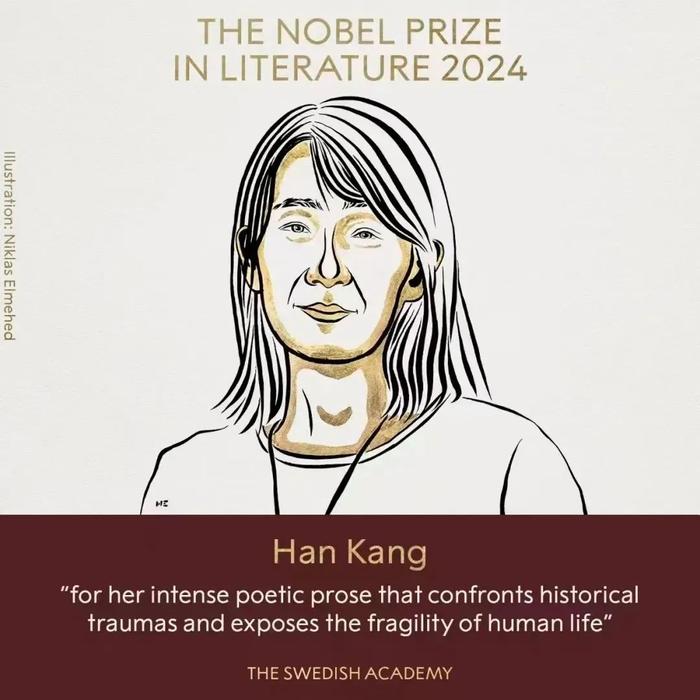
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
正如颁奖词所言,她善于克制、平静的语言,描绘根植于日常生活里不可脱卸的伤痛与绝境。疼痛,是韩江的作品带给人的第一印象,扒开这层疼痛的皮,看见的不是喷涌的血流,而是挣扎着跳动的毛细血管和伤痕累累的筋骨,静默流出生命冷冽惊悚的底色。
韩江出生于1970年的韩国光州,迄今为止算是相对年轻的诺奖得主。她自25岁起就开始出版小说,早已拿遍韩国国内各大顶尖的文学奖,2016年她凭借《素食者》拿下专业级的国际布克奖,成为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足以证明其文学技艺和艺术水准。
这也是她在华语读者群体中最为出名的代表作。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第一次阅读《素食者》时感受到的那种深刻而真实的疼痛感,小说没有复杂的人物与情节,却构建了一种似与读者呼吸相贴的日常的暴力:一个家庭主妇,为摆脱家庭暴力,渴望变成一株植物,为此,她拒绝进食,只饮水、吸收阳光,直到生命几近枯竭。她用沉默和静态的方式,退出人类世界,让出自己备受操控和凌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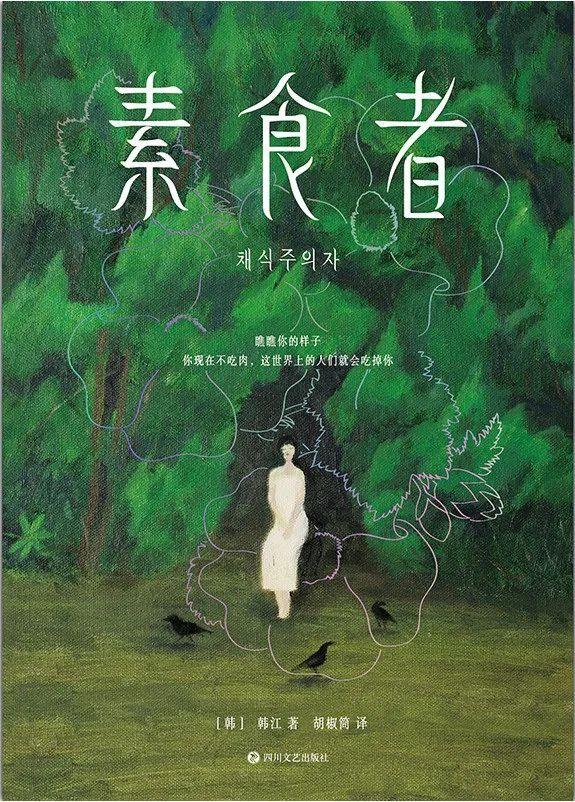
韩江《素食者》
这是一本易读的小说,但绝不是一部能让人舒舒服服看下去的小说。相较于诺奖的颁奖词,她在2016年发表的布克奖获奖感言,更贴合她普遍的书写主旨: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探讨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
对人的本质的挖掘,是韩江在历史运动、女性处境外衣下包裹的终极内核。从光州暴力到家庭内部的个人暴力,她的书写宛如从地里长出来的某种植藤,不浓墨重彩,但茎脉全都丝丝入扣,用一个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垮塌,暗喻她在整个社会以反抗姿态的沉默退出。
诺贝尔奖迄今120余年,每年文学奖的预测与揭晓往往最为激烈。相较于其他学科的奖项,文学的评价标准似乎更为复杂,且往往掺杂相对主观的判断。而按照阿尔佛雷德·诺贝尔生前遗嘱里的说法,文学奖应当颁给那些“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从“品质”到“贡献”之间,最关键的一道标准,是创作者是否具备直接触探人的存在形式的视野,是否具有自灵魂深处启迪人类社会的可能性。
从形式上看,书写是一件私人的事,但隐秘的起点最终通往更广阔、普适且深入的人类灵魂深处。这是文学在文明之上开的花。而女性写作与女性作家近年来在诺贝尔文学奖中占比升高,并不能反映所谓“女性主义”的胜利,因为韩江的视野,远不止于性别。

暴力一种
从某一天开始,英惠开始渴望自己变成一棵树。她不再吃肉,只吃极少素食和水,感受着自己的生命慢慢枯竭。
英惠是一个普通的韩国家庭主妇,重复着和多数韩国主妇一样的日常——做饭、做家务,照料丈夫的生活起居,以及保持沉默。某一天,她开始不断陷入可怖的梦境。她在梦中杀人、吃生肉,展现出原始野蛮的一面。梦醒后,她开始渴望变成一棵树,并不再进食肉类。
然而,当英惠向丈夫复述自己的梦境,得到的却只有不解和不耐烦。她的变化和话语,鲜少被家人注意到,无人关注她的疼痛和绝望,亦不见她内心的干涸与枯萎。面对她日复一日消瘦和虚弱的身体,丈夫、父母都只觉得厌恶和恼怒。

书中有一处细节,一天早上,英惠在丈夫气急败坏的催促下切肉,不小心切伤了手指,鲜血流出来,同时,刀刃掉了一块碴。可丈夫根本没关注到英惠的手指,而是对烤肉里的硬块暴跳如雷。他对妻子大发雷霆,斥责她想要杀死自己。
而当英惠开始吃素,并拒绝与丈夫进行身体接触后,丈夫也并不关心任何实质性的原因,而是粗暴地强奸了她。
在英惠自己的家中,她也未能摆脱父权制的野蛮控制。面对不愿吃肉的女儿,英惠的父亲直接对她大打动手,还试图掰开她的嘴,强行将食物灌进嘴里。
英惠是文学意象上更具现代性的“疯女人”。她的“疯癫”始终是沉默和冷酷的,面对冰冷扭曲的所谓现代文明,她用拒绝和退出,而非进攻与讨伐的方式,完成了反抗。
“变成植物”,是对“好妻子”“好女儿”身份的脱离,也是一种对自由和解脱的向往。极端地食素,重构了英惠与真实世界的联结,弃掷了她原本被世俗期待的、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个女人所能触及的最简单直接的反抗方式。
书中有一句少见的直白的台词:“你现在不吃肉,这个世界就会吃掉你”。成为植物,是为了回到人的本质,为了摆脱现代文明社会对人的暴力和欺辱。然而,是否只有故事终端的死亡,才能让她短暂拥有自由,免于暴力?
早在1997年,韩江就已经构想过一个“变成植物的女性”的故事。彼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植物妻子》中,一个浑身瘀伤的妻子,随着创面的逐渐扩散,最终变成一株绿色的植物。

韩江《植物妻子》
2016年,韩江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对人类的暴力本性与能否克服这个本性的问题”,而创作《素食者》,是希望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人类的残忍、暴力与冷漠,不过是借由随处可见的女性困境浮出水面,“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
本书的英文译者黛博拉·史密斯则认为,韩江的写作动力,大多是探讨“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探索创造一个纯真世界的可能性”。
借植物或动物喻人,是韩江惯用的构建“纯真可能性”的寓言实验。她的另一部代表作《玄鹿》,描写一座煤矿城市的衰败,以及对家乡失落的人们的焦虑与茫然。“玄鹿”是黑鹿的意思,“我们人本身就是玄鹿,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寻找光明。”
暴力始终是韩江书写的核心主题,而她对暴力的反思,多从人而非社会的角度。平实的文字犹如藤蔓,但总能丝丝入扣,缠绕到人心深处,形成一种难以脱身的刺痛和共振。

顽固的疼痛
一直以来,韩国文学在东亚文学界是相对边缘的存在。以时尚、流行文化等工业产品闻名全球的现代韩国,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常年居于冷门。尤其是在华语文学、日本文学面前,韩国似乎总是人微言轻。
可将视域缩小到韩国内部,用艺术对社会、人的处境作出反思,其实在韩国已积攒了相当丰厚有力的创作土壤。比如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现实主义电影,用深刻犀利的寓言式的抨击与批判,揭露社会千疮百孔的创面。
而作为韩国最具国际声望的70后作家,韩江的书写,并不建立在单一的现实主义之上,而是具备相当明显的现代性。植物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人,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半隐半显在轻盈的文字里。
2016年,《素食者》获得布克奖之后,韦氏词典网站就曾根据热词搜索发现,“卡夫卡式”一词在颁奖给《素食者》之后搜索量激增——这是一种对二十世纪聚焦个体异化的文学传统的回应。
1970年11月,韩江出生于韩国光州一个文学世家。父亲和兄弟都从事文学工作。韩江的丈夫洪荣熙,也是韩国庆熙网络大学的教授兼著名文学评论家,他曾这么评价妻子:“每一个句子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对自己异常严格,具有惊异文学锐角、激烈文学追求的人”。

1993年,韩江在《文学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几首诗,从此开始写作生涯。她曾表示,自己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写诗让我进入情绪”。可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深刻造诣,使她的文字早早脱离了个人的、情绪的书写,进入到更宏大的人类命运的观照当中。
2014年出版的《少年来了》,聚焦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光州民主运动。与更广为人知、更贴合时代情绪的《素食者》相比,前者描写更直接的杀戮和暴力,但无论是宏大的历史主题,还是家庭内部个体遭遇的精神和情感暴力,它们在浓度与程度上,其实相差无几。

韩江《少年来了》
《少年来了》里借少年之口讲述暴力带来死亡后的一种反思:“我们在观看往生者时,其灵魂会不会也在一旁看着他们自己的面孔呢?走出礼堂前,你回头巡视了一番,不见任何灵魂踪影,只有沉默仰躺的遗体,与臭气冲天的腐尸味。”
这种将人和躯体、生与死放在同一平面对话的描述手法,与《素食者》里肉身和植物的对照类似,是韩江所擅长的某种对现实边界的打破。2018年再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集《白》里,“我”置身二战后残余废墟的波兰华沙街道,忽然感到“城市就像是一个人的从死到生”。这部书里,韩江让在自己出生前就死去的姐姐复苏,让生与死对话。

韩江《白》
在韩江出生前,她还有过一个仅出生两小时就夭折的姐姐。韩江出生后,身体也常常处于虚弱状态。从十几岁起,韩江就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当疾病发作,她便不得不放下任何工作,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乃至如今,她都不得不时时与疾病对抗。
自幼对生命的持重和敬畏,倒是为韩江的创作带来了某种动力。“如果我100%健康并且精力充沛,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虚弱和疼痛,以及由此引发的联想和拓展,以一种奇诡独特的视角,进入生命体验的内在思索。
在所有描写女性处境的东亚文学里,当代韩国文学的风格渐渐独树一帜。从写出《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年热门同名电影的原著)的赵南柱,到近年来在中文世界渐渐为人所知的韩江、崔恩荣等小说家,韩国创作者对女性处境的反思,往往尖锐地集中在家庭内部,描绘那些被家庭吞噬的女性。

赵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
相较于在中国具备一定探讨基础的“出走”,文艺作品里的韩国女性,更常面对的结局是死亡、麻木或接受。
在这当中,韩江的反思,具备一份独特的冷冽与深刻。但如果将其理解为粗暴的“女性主义”的胜利,则舍本逐末地拒绝了本可以深入更广阔层面的“人”。

女性作家与诺奖
今年的诺奖,似乎在有意改变其自身苍老的形象,拥抱潮流和热点。比如,物理奖、化学奖,都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可谓紧扣时代热点,回应当下的社会关切。
文学奖再次回到亚洲,给了一个不在欧洲主流视野、相对年轻的女作家,既是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诺奖百余年,我们能看得到它在不断拓展的边界和可能性的尝试。比如,2016年轰动全球的首位音乐人获奖者鲍勃·迪伦。与其说,这是一次对音乐歌词文学性的褒奖,不如说是诺奖对流行文化的萃取,以及对反文化运动的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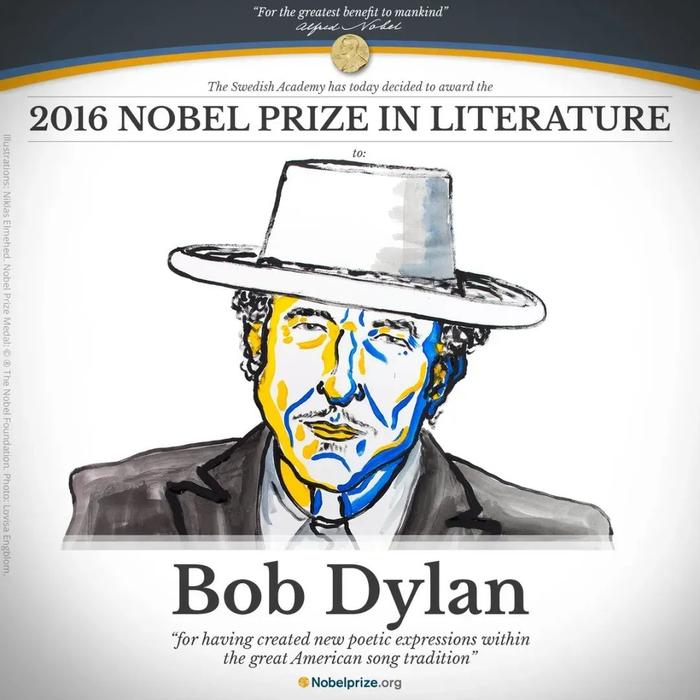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流行音乐偶像鲍勃·迪伦
更深层次,诺奖也需要证明自己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价值和影响力,它似乎想表明,广义的“文学”,从来不单一地指代写作,而是涵盖所有对生命灵魂本质与时代文明作出折射或启迪的载物,这是属于诺奖才能定义的文学价值。
的确,韩江能被世界看见,离不开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女性主义思潮。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更多考虑全球总体性,重视文学作品的创新思想和时代特定议题,比如受重视程度肉眼可见上升的女性写作。
2017年往后的7年内,有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颁给了女作家。在过往的诺奖史上,近十年来的女性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度。
不过,若说女作家获奖,仅仅是吃了社会思潮的红利,则是天大的误解。相反,她们创作层面的技艺水准、思想深度和视野,一点也不输顶尖的男性作家。
如2018年的诺奖得主,波兰国宝级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十分擅长在小说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观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其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更是包罗万象,前者折射波兰二十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后者有着宇宙天地的广阔哲思。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2022年获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则通过一系列基本上是自传体的作品,为一个战后随着法国社会的动荡而发展的女性的私密生活制作了一幅出色的透视图,精巧地编织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书写了关于个人、记忆与集体困境的宏大诗篇。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从这些作品来看,作家所能达到的成就,也许无关性别,但性别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毕竟,文学是语言、生活、社会、历史的总和,文学是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对话。经验的主体性、对话的主体性,决定了文学版图的边界和疆域。长期以来,这是男性作家所主导。
与其说,女性作家需要被诺奖看见,不如说,老气横秋的诺奖,需要女性作家去拓展自身的价值,补全文学版图的疆域。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双赢。
诺奖评委之一的艾伦·马特森(EllenMattson)曾在访谈中讲述评选标准:“世界上到处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你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成为获奖者。很难解释那是什么。我想这是你与生俱来的东西。浪漫主义者称其为神圣的火花。对我来说,这是我在写作中听到的一种声音,我在这位特定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诺奖未必能代表主流,但将一项备受全球瞩目的桂冠颁给韩江这样的作家,何尝不是对文学所承载的社会价值的一次拭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