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人”的应然形象评《私法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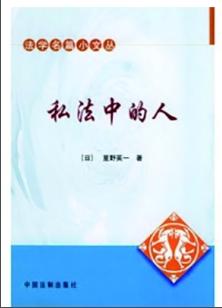
■《私法中的人》
作者:(日)星野英一
译者:王闯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经历着变革。”法作为笼罩在人类社会的“无形大网”,注定会被数字时代注入新的因素
□尹铭育邓伊鸿
“人”长期以来是古今中外不同领域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关于讨论“人”的作品早已卷帙浩繁,但对于探赜“人”的热情不减反增。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的论题几乎是自古既定的。所谓的不同,大多在于研究方法或者语言范式的不同”。星野英一作为一名日本法学家,同样尝试运用法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呈现出法律中“人”的形象。
整体来看,星野英一通过历史叙事方式,并聚焦私法领域来刻画法律中的“人”。具体来说,他很大程度上将目光投向《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通过揭橥寓于两部法典中不同的人格涵义来定位法律中的“人”。
从古罗马到数字时代
在星野英一的语境,他通过对《法国民法典》的考察刻画出私法中“抽象人格”的形象。而后,对《德国民法典》的考察则引出寓于“人”形象中的道德伦理性。不可否认,他的确在自我限定的近代以降这一时间范围内,揭橥私法中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形象。
然而,私法中“人”的形象并非是一座“飞来峰”。正如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所说:“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与民族的初始状态保持生动的联系,而丧失了这一联系,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限定时间范围导致星野英一无法析出私法中“人”的整体形象。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松绑”他在时间维度的限制,向前追溯到实质意义上出现私法中“人”形象的罗马法,向后自然延伸至数字时代私法中“人”的形象。
公元3世纪时,古罗马法学家赫尔墨杰尼安曾提出:“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人而制定。”这里的法律实际上就是罗马法。检视罗马法的内容,其中的确已经涉及有所谓“生命人”以及“法律人”的相关内容。
实际上,罗马法秉持的不是“法定权利”的理念,而是法律表达出人在群体中生活的状态。总而言之,寓于罗马法中的“人”并不是星野英一已经刻画形象中的任何一种。相形之下,罗马法中的“人”并非是单独的个人,更多是以与人相关的集合概念呈现出来,例如,家庭、公民等。
“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经历着变革。”法作为笼罩在人类社会的“无形大网”,注定会被数字时代注入新的因素。同时,私法中的“人”作为法的一个切面必然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
不可忽略公法中的“人”
星野英一确实直面私法中“人”的形象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不可否认,抛开时间维度的质疑,其在内容维度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可取性。同时,基于其民法学者的身份,这样的技术性处理就更能理解。
然而,这种技术性限定并非自明之理。更何况,星野英一在序言中首先提出其他视角的瑕疵,而后才转向的法律视角。逻辑上,后者应当相较前者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从其论述中很难感知到一二。从序言中随后的限定来看,甚至看出他企图通过阐明民法上的“人”来刻画法律中的“人”这一不切实际的追求。
目前,关于法律的划分并未达成高度的共识。不过,公法和私法划分基本是人们所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纯粹的逻辑维度,私法中“人”的形象上升至法律中“人”的形象是以偏概全。当然,也不宜直接通过逻辑周延性来否定这一方式。毕竟,完全存在公法中“人”的形象与私法中“人”的形象基本重合的情况。在这个维度中,以偏概全也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对此,需要突破私法的畛域,聚焦透析公法中“人”的形象。
星野英一对《法国民法典》的解读,就其宏观背景而言,大致定位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后,也就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法国《大宪章》里都闪烁着“人”的光芒。整体而言,这些规范里的“人”多是坚强的、自力更生的、“独行侠”式的个人形象。从这个维度来看,公法中“人”的独立形象与私法中“人“的抽象平等是不同的。
在对《德国民法典》的解读中,星野英一立足于德国的特定语境,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十分注重《德国民法典》中有关“人格”的解读。这似乎与世俗自然法与康德哲学等支撑的“个人与社会融合关系”中的公法权利观相契合。星野英一基于“人格”的相关理论,对私法中“人”的形象予以修正。而“人格”本身就蕴含尊重“人”的实质内涵。从这个维度上说,私法中的“人”似乎与公法中的“人”相重合。
遗憾的是,这种解读实际上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为,星野英一的修正引入的所谓的“倾斜保护”,其已经超越了法律的场域,而深入到伦理学的领域。笔者认为,将私法中“人”的形象等同于法律中“人”的形象是陷入“范畴错误”的泥沼。
伦理的而非法律的
有趣的是,星野英一关于法律中“人”形象的结论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维度与逻辑维度的补足而崩溃。反之,他序言强调的“人虽是肉体的存在,但其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是具备理性和意思的,可谓是伦理的存在”的结论更得到了补强。
从直觉来看,这一关于“人”的形象似乎具有极高的可接受性。从功能上,这一形象也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能够为“人”在遭遇各种不测时寻求一块安身立命的乐土。固然,“人”的这一形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无法否认,这并非是对法律中“人”的形象的回答。
简言之,星野英一面对私法中“人”的形象看似答非所问。有人甚至认为,他运用伦理性的答案回答法律问题的做法,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法律中“人”的形象。
如此抽象的指摘可能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鲜明的例子便能轻易拨开其中的迷雾。德国公法学家耶利内克曾讽刺过这种杂糅:“当法学家说国家是‘人格人’时,运用生物学方法的人会说,国家没有头没有脚,所以不是人;而同样的生物学方法的运用却又会说国家也如同细菌、牧草、哺乳动物一样是有机体。”
实际上,回归“人”的形象本身,相关的例子也能让人恍然大悟。在生物学上,“人”不过是灵长目人科人属物种。但要是以这样的回答去应对法律中“人”的形象之问,人们必然难以接受。实际上,面对法律中“人”的形象之问,以生物学还是伦理学作为答案并没有质的不同。
从情感的直觉角度,不可否认伦理性的回答明显会比其他面向的答案更容易令人接受。伦理维度强调“人”不是动物,不是机器,不是一件物品,不是其器官的集合。法律面向中“人”的形象与伦理中“人”的形象具有某种亲缘性。两者重叠部分难免会给人“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对此,更需要审慎区分“人”的形象。
(作者单位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责编:尹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