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归去来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诗经》归去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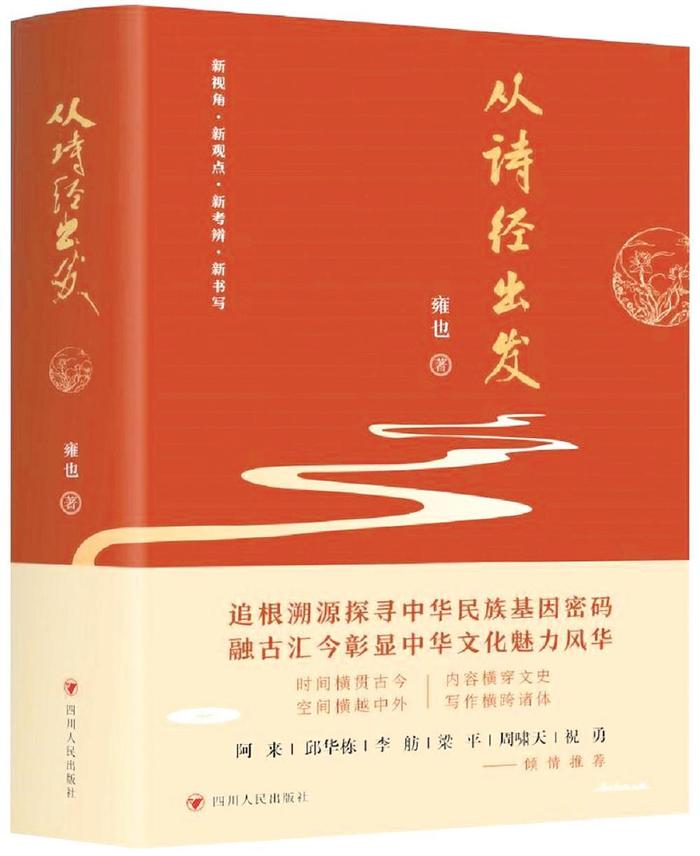
□林赶秋
《诗经》是诗,是经,是元典,是大IP,是显学。因此,从孔夫子、大小毛公以迄于今,围绕《诗经》衍生出了浩如沧海、郁如邓林的各种论著,使人应接不暇,皓首难穷。另外,“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也有很多书打着《诗经》的幌子贩卖私货,什么“诗经里的情事”“诗经里的恋歌”“风情万种说诗经”“在最美诗经里邂逅最美的爱情”等,啰啰唆唆,重重复复,由于销量不少,给好些不看原著的读者似乎都留下了一个《诗经》只是一本爱情诗集的印象。针对文学创作领域中趋易避难的时尚潮流,余华先生曾提出要对生活进行“正面强攻”,而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图书则是对《诗经》的侧面游击、借壳上市,只一味追求表达上的文学性、故事性与猎奇性,对《诗经》原文及其内涵不但缺乏整体的把握、深刻的领会,且常常跟在权威屁股后面打转,鲜有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识。
有别于此,作家雍也《从诗经出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一书大胆跳出“文学”的窠臼,勇敢潜入“文化”的汪洋,务求恢复《诗经》作为传统文化元典的原貌,并在全球视域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既勠力发掘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一面,也随处剔抉其差异,以反观自照,最终“在融古汇今中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风华”。
在古代社会、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人类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采取类似的路径而进行的;在相同的情况中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所有人类种族的脑髓机能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精神的活动原则也都是相同的。”例如天命观,即是人类共有的精神活动之一。《诗经·大雅·文王》响亮地唱出了诗人的心声与当时的最强音:“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此正可与《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句连类。换言之,在“有周一代”或《诗经》时代人们的意识内,“天命”是变化无常的,“天”亦不特别跟谁亲近、为谁停留,要想获得它的护佑,还须自己积“德”。《从诗经出发》认为,由《文王》此句发轫,渐渐演变为后世恒言的“安天命,尽人事”,成为“历代中国人的主体思维方式”。然后,《从诗经出发》又将其与希罗多德《历史》、柏拉图《蒂迈欧篇》等记载的天命观进行横向比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西两种天命观有一个共同点——人都受命于天,被其主宰。但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天命观的宿命论色彩要“重得多”,中国天命观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则“强得多”,为了加深理解,雍也补充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本身就是命运天平的重要砝码。”
书中对诗经中蕴含的龙文化、玉文化、水文化、君子文化、饮食文化、婚恋文化、战争文化等都做了仔细梳理,并上溯下探,昭示了华夏民族在童年时代的风采神韵,探究了中华民族在其童蒙时代的气质禀赋,实现了作者追求的“在追根溯源中探寻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于今人而言,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诗经》作为文化元典的秘密,其实古人早早就做了提示。孔夫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太史公曰:“《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在铿锵韵律抑扬顿挫之间,《诗经》也顺道将那个时代的万物万象包罗其中,由此也就诞生了诗经名物之学。既有出于对名物学的喜爱,更因其农民之子的身份,雍也特别留意《诗经》对粮食作物的描述。在《〈诗经〉谷麦叩响的记忆》一篇中,雍也凭借大量的笔墨深情追忆了小时候长辈面对新谷米的欣喜和郑重。他说:婆婆拿新米饭供奉祖先的举动和言辞,或许正是《诗经》“烝畀祖妣”等古风“在漫长岁月、广袤大地上不绝如缕、隐隐约约的遗响”,而“家乡家家户户用新米或新收获的高粱酿制醪糟酒、呷酒以自用或待客,这亦是家乡与《诗经》‘为酒为醴’之风隐隐相通之处”。说到用谷物祭祀,不禁让人想起旷世奇书《山海经》的一段:“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大意是讲,四川岷山一带曾流行瘗埋“稌”以祭山神的习俗。有趣的是,《诗经·周颂》亦称稻为“稌”,似可旁证《山海经》此段定稿年代颇早,即便不与《周颂》同时,至少也不会晚到通常以为的战国期间。
雍也从《诗经》出发,于时间上横贯古今,空间上横越中外,内容上横穿文史,体裁上横跨诸体,初心是为了追根溯源,以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思想密码,却在上下求索的同时无形之中回归了《诗经》文本乃至“诗经现场”,没有挂羊头卖狗肉的信马由缰、信口雌黄,多有由《诗经》而当下的有机延展、有序联想,使读者得以与他一道站在21世纪的通衢大路上,侧耳倾听,提灯辨识这一部由风、雅、颂合奏交响的、从华夏民族童年穿越历史烟云飘飞而来的天籁一般的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