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明末中国知识分子承受西方的影响,在清代并没有消失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历史学者孙立天撰写的《康熙的红票》一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掘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耶稣会会士自从明末进入中国,为天主教传教,却也同时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传入中国。这一段过程,乃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交融的过程。对于中国终于从相对孤立的东亚大帝国,牵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以下是许倬云为《康熙的红票》所写的评论。
撰文|许倬云
(历史学家、美国匹茨堡大学荣休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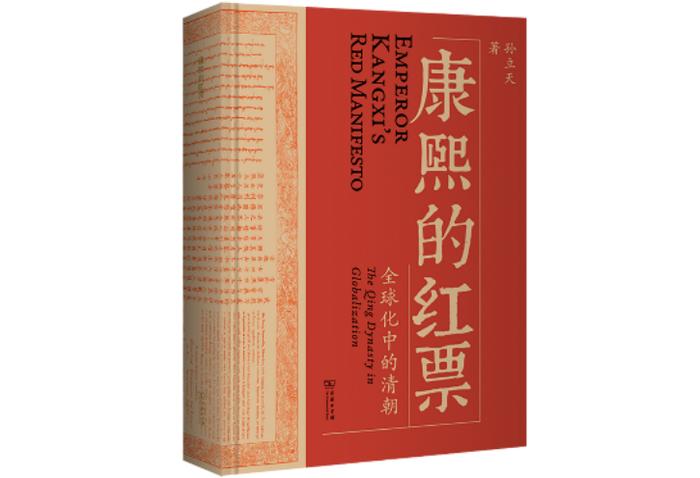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
作者孙立天撰写的本书,乃是讨论耶稣会会士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皇室之间的互动。
耶稣会会士自从明末进入中国,为天主教传教,却也同时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传入中国。这一段过程,乃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交融的过程。对于中国终于从相对孤立的东亚大帝国,牵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李约瑟这一研究古代中国科技史的重要人物,认为这一段中西交往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长达百余年的接触,访华教士以耶稣会会士为主:他们是天主教传教士中,学问最好的一批精英。然而,这些接触,却并没有发挥巨大的力量,为中国与西方互动铺下足够的基础;以至于后来,中国对于西潮的反应,却是以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冲突,作为最后不幸的结局。
李约瑟的疑问,确实是中西学界无人能规避的课题。最初提出答案的方向,乃是法国谢和耐的著作《中国和基督教》所提出的文化冲突,成为主要的障碍。这一构想,长久以来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会士的努力定下来“遗憾”二字。
孙立天撰写本书,却是提出另一个想法:至少在清代前期,天主教士与清朝皇室其实交流顺畅,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而天主教士,也的确将天文、历算、数学、舆地、绘画、建筑各方面的知识,带进清皇朝的种种活动中。
孙立天提出来的构想,特别指出:在清初四代,耶稣会会士并不像利玛窦的时代,与中国的知识界有直接的互动,乃是经由那时候特别的机缘,一变为皇室自己的内廷中相当于家仆、包衣的身份;他们的活动,见诸于内务府,而不见于朝廷、内阁。
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密切。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负责天文、历算、医药,以及作为西方知识的介绍者,参与皇子们的教育,有时也会卷入内廷的争斗。
孙立天在书中指出的特点,确实可以解释:如前所述,为何清代的天主教士没有如明末那般,和社会上的知识阶层有密切来往。他们的贡献,小则如上述天文、医药等方面知识的传授和应用,大则他们会替内廷设计大炮、火枪。
孙立天所举的史料,例如康熙的“红票”,乃是皇室直接经由传教士与西方各国交往,甚至于征求他们送来更多的学者,等等。传教士也直接介入清朝皇帝的对外活动,例如:清朝与沙俄之间所定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首次对外的国际条约,乃是由传教士担任谈判代表,维护中国的利益;而这一任务,几乎完全脱离了外朝政府的掌握。
孙立天提出的这一类特点,也的确如他指陈:传教士是皇室的包衣,他们实乃家臣也。同时,虽然清代杨光先那一类的保守分子,攻击传教士背叛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但这一事件,相较于明代中西知识分子广泛而普遍的接触,以及明末传教士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言,其重要性不能同日而语。
我有两点构想,提供读者参考,也希望孙立天先生,将来另有著作的时候,加以考虑。第一点,明末中国知识分子承受西方的影响,在清代并没有消失。中国明代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甚至于方以智等人物,因为西方传教士带来新的角度和思想,编著了许多实用科目的大书,例如《天工开物》等。明末许多重要的学者,在心学理论以外,不少人注意到实用的课题,例如顾亭林的《日知录》等书,以对社会与知识的实用部分的讨论,作为他们治学的重点。也有许多学者注意到社会思想的重要课题,例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一类的著作,就是上面所说的例证。东林学派除了讨论儒家的淑世精神,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他们关心的项目。
第二点,我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他们统治的帝国始终是一个二元性的结构:汉地是中国的主要部分,而在经过几次大征伐,收服了蒙古、回部与西藏——这些汉人以外的世界,乃是北方草原上的“另一个帝国”,而大皇帝是所有北族共同的“大汗”,西方传教士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归顺的北族而已。
在这种结构下,传教士与顺治、康熙甚至于乾隆关系亲密(雍正信奉喇嘛教,对天主教并不亲密),也因此他们能够参与王子们的教育,参与建造圆明园这种大工程,担当清朝与沙俄之间的外交任务,也成为并不很清楚的西方世界与满清大汗之间的接触点。
上述建议,并不是否定孙先生大作的创建:传教士与清代皇室的亲密关系,界定了他们的特殊地位。我只是希望读者们能够理解,清朝政权的复杂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也非初见。
举例言之,大唐盛世,中国皇帝乃是四裔的“天可汗”;而唐代的军队,有极大部分不是汉人的军队,而是各种外族整族成为唐室的武装力量,或者以杂胡的身份从军争战。中国的历史,其实不是《资治通鉴》的体例可以完整涵盖的。
以上这些是我以读者的身份,向本书的读者们提出一些常被史家忽略之处。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许倬云;编辑:荷花;校对:柳宝庆。封面题图素材为纪录片《他与帝国同行》画面。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