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处的艺术
▌周家望
100岁的李滨声先生又出新书了,书名叫《跟自己玩儿》,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书的样式设计成一个“Z”形:一半是蓝色封面的随笔集,一半是红色封面的漫画集,随笔集和漫画集的封底,“背靠背”地合为一体。就好像一个穿着蓝衬衫、红裙子的小姑娘,亭亭玉立地往那儿一站,透着那么珊珊可爱。冲这书名和设计,谁见了都说“老爷子真会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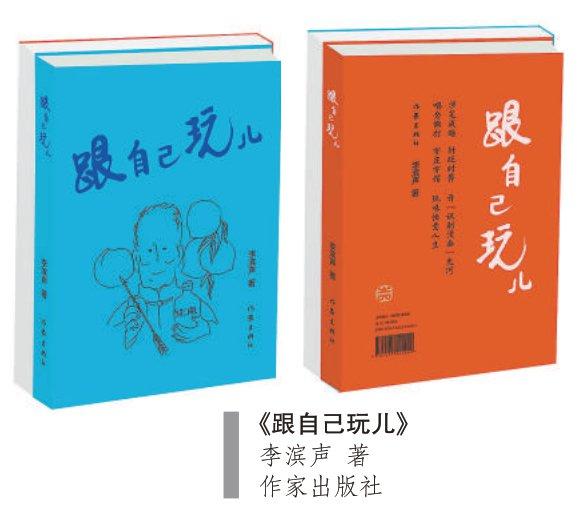
“跟自己玩儿”是门学问
玩儿,谁都爱,那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会玩儿,可就高级了,既需要与生俱来的天分,也需要身上的勤奋,还需要心里的不安分。所谓“天分”,就是艺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祖师爷赏饭”,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材料。所谓“勤奋”,就是爱因斯坦说的“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张恨水也说过“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所谓“不安分”,就是脑子里时不常有千奇百怪的新念头,总有奇思妙想的新尝试,培根非常赞赏这种不安分,他认为“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墨守成规将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不安分”的人,往往是社会进步的先行者,是时代风尚的引领者,是文学艺术的首倡者,是生活味道的寻觅者。千百年来,那些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往往是“不安分”的人,他们的脑回路或许迥异于常人,更强大,更自信。
光“会玩儿”,还不行。学会跟自己玩儿,才是真正的“王者”。您想啊,人生在世,步履匆匆,一路之上,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父母、兄弟姐妹、恋人夫妻、同学同事、师生朋友、儿女孙辈,乃至旅途偶遇,或多或少都陪伴你走过一段生命时光。但从头走到尾的,其实只有你一个人。老话说,谁也不能陪你一辈子,一点不假。之所以人是群居动物,正是因为孤独之心,人皆有之,概莫能外。因此学会跟自己玩儿,就是不自陷于万古孤寂中的逃生绳。
跟自己玩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玩儿法。你首先得具备一个“有趣的灵魂”,然后打开那扇“跟自己玩儿”的门,全身心地沉浸其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王国里,你就是国王,尽可以率性而为,流连忘返,乐不思归。这个时候,你根本无暇顾及那无边的寂寞,不尽的孤单。你心里的那个我,和外在的那个我,早已经玩儿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前仰后合。自嗨才刹那,世上已百年。你会觉得,时间为啥这么紧巴,还没玩儿够呢,就“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啦?
当然,您要能玩儿出点名堂来,那可就更不得了喽。不管是书法、绘画、做木匠活儿,还是弹琴、种花、写文章……只要沉得下心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可以解释为,跟自己玩儿的“剩余价值”。恍惚记得有位前辈老先生说过,无论做什么,积之十年,总能成一学者,哪怕是收集糖纸或火花,也能看出这十年间的社会变迁。是鲁迅先生说的吗?真记不清了,好像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在摘抄本上记过,一直存在脑子里,意思大抵是不会差的。

绝对的“段子高手”
“会玩儿”的李滨声先生,绝对是“跟自己玩儿”的魁元,绘画、书法、魔术、票戏、民俗、诗文,无一不精,无一不妙,别开生面又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而世所公认。从他给自己这本书写的《前言》,您就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这个《前言》只有138个字,而且还是白话文。不妨抄录于此:
“英文‘中国妇女出版社’版李钟秀女士曾写过一篇长稿发表在《北京日报》,题目是《看李滨声表演魔术五十年》,是一篇趣味随笔。
魔术是我爱好不假,不过自从退休后早已不再实践了。倒是近十多年来由于住养老院又遇疫情,生活单调,与我好动习性不符,为自己计,常温故技魔术表演度时光。有时也写点随笔远近见闻,不成文字,不过跟自己玩儿。”
怎么样?既不故作深沉,也不故弄玄虚,既不掉书袋,也不吹牛皮。我以前觉得,有些人写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的冗长文章,无非是挥霍自己的生命,浪费别人的时间。后来从新闻岗位转到五色土副刊工作,耳濡目染,渐渐觉得好像文章中不引用几本古籍或译著,不拉上几位前人或洋人,就像鼻子上缺副金丝眼镜,腕子上缺块闪闪发光的名表,手上缺根乌黑油亮的文明棍。缺了这些就似乎上不得“台面”唬不住人。所幸读了李滨声先生的《跟自己玩儿》,总算又把我从“台面上”拽了回来。有道是“老僧只说家常话”,这本书里面没有枯涩的说教,没有傲然的睨视,只有生活的智慧和会心的一笑。《跟自己玩儿》的文字率性天真,极具漫画效果,李老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
李老是绝对的“段子高手”,他的随笔精短有趣,却又回味无穷,正如同他的漫画,能做到极简的妙不可言。捧读这本《跟自己玩儿》,我经常“噗嗤”一笑后,转而赞其文笔之精彩。比如开篇《我和外交部长握过手》中他的“反省”:“当年为什么在严肃的场合放肆说‘去过通州’?是有感那位画家扬言‘去过非洲’,我以为其好表现。其实自己也是好表现的,只是没有表现的资本。”比如不足400字的《袁三倒煤记》,读完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汪曾祺的小说《陈小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喷气式”》中,他对善恶报应的对比感悟,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再比如《我曾当过和尚》中首次披露,九十多年前他曾当过“寄名和尚”,五岁那年还的俗。同样有趣的是,在本书中,李滨声先生像孙悟空那样会“七十二变”:“我”“文教部的干事”“文艺处的一小青年”“某人”“李某”“某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不同的描述情境中他的身影随时隐现,变幻无穷。当然,为了顾及一些当代名人的颜面,李老在文中也隐去了某些人的大名,比如《不是“张冠李戴”》一文中以“诗”批斗李滨声的“大作家××”。
这本书里,还有一部分图文是关于旧京知识和民俗文化的,也体现出李老的文字纯熟和博闻强记。例如《建国门、复兴门、和平门史记》,这篇史记,只用了区区500字,就把老北京九门之外的三座门讲得一清二楚。《长安街史话》,更是只用了350字即勾描完毕,真可谓惜墨如金。
当然,书中也给我留下了些许问号。比如《民初“文明结婚”啥样?》,讲了新式婚礼的一应礼仪,只是文中有一句语焉不详:“新郎新媳妇谢家长也是三鞠躬”,这里说的“家长”,是否包括新娘的父母呢?因为中国古时的婚礼,娘家父母是不把女儿亲自送到婆家的。只有新姑爷三天“回门”,小两口才回来拜见泰山泰水。那么民国时期的新式婚礼,是否跟北京现在的风俗一样,双方父母都在场共同见证呢?期待《跟自己玩儿》“二刷”时读者能找到答案。另外,因李老毕竟年事已高,书中有些人名偶有舛误,如“翁偶红”应为“翁偶虹”,“司马一萌”应为“司马小萌”,“北京晚报社社长王纪纲”应为“北京晚报总编辑王纪纲”(北京晚报隶属于北京日报社,只有编辑部)等,期待再版时调整过来。
已经玩儿了一百年
虽然我和李老都是北京日报社的职工,但在工作上没有交集。余生也晚,他1987年离休的时候,我还在北京一中读高中。我和李老混熟了,还是我做北京晚报跑政协新闻的记者之后。
那时他也是政协委员里的活跃分子,会议之余,变魔术、讲笑话、画肖像,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总有一群热情的“粉丝”围着他笑声不断。在政协的一楼大厅里,给委员们画速写漫画;在政协联欢会上表演拆解“九连环”的魔术,我都在现场亲眼得见。
后来他搬进了敬老院,我就隔一两个月去看望一次,从昌平的汇晨老年公寓到顺义马坡的家泰养老分院,再到天通苑的家泰养老院,一路追随。相见亦无事,就为了听老爷子聊京剧的林林总总、聊报社的老人旧事、聊老北京的史地民俗,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到五色土副刊工作后,他又成了我的年龄最大的作者,并且专门开了个“梨园客说戏”的不定期小栏目。每篇文章他都用正楷誊写后,通过微信拍照发给我。我再重新录入电脑交给编辑刊发见报。
这些年,养老院去的次数多了,我渐渐感受到了人到老年的孤独。许多老人坐在轮椅上,歪着脑袋,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一坐就是大半天,悄无声息。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平添了一层落寞。想想看,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寿星,或许当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英雄暮年,不过衰翁。和他们相比,李滨声先生就活得更充实些,每天练字、画画、写文章,忙得有时都错过了饭点儿。
这两年,他又学会了在微信刷视频忙点赞,有时候半夜两三点还那儿点赞呢,真是服了。当然,不忙的时候,老爷子也弄杯小酒喝,或是来个冰激凌放松一下。李老爱吃零嘴儿,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吃酸辣笋尖,跟我聊着天,就能把小半袋笋尖吃完。
有人说,李滨声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市宝”“国宝”。看着他吃笋尖的可爱劲儿,我就想,莫非“国宝”们都爱吃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