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雅嘎下了个蛋|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芭芭雅嘎是女巫,但不属于女巫的团体;她既可以是善人,也可以是恶人;是母亲,也是杀死女儿的凶手;是女人,但没有、也从未有过丈夫;她伸出援手,也策划阴谋;被人类社会驱逐,也与人类沟通;是战士,但也操持家务;是“死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她会飞,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地面上;她只是个“偶然出现的人物”,却也是主人公通往幸福之旅的关键一站:“礼貌的”和“粗鲁的”主人公在她的小屋前驻足,他们吃饱喝足,舒服地洗个澡,听取她的建议,带走她送的魔法礼物,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翻译成更现代的语言,她是异见者、流放者、失败者、隐居者、老处女、丑八怪。她的形象依赖于口述传统,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一面集体的镜子。她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好的时代,那时她还是金色芭芭、大地之母。后来,她成了被驱逐的稻草人,但依然用诡计统治着人们。如今,她缩在小屋中煎熬时日,像子宫中的胚胎,或棺材里的尸身。
没有一个人带着花和巧克力,再次敲响她的门。
在杜布拉夫卡的笔下,芭芭雅嘎是斯拉夫故事中被刻板化、压抑和丑化的女性角色,她分析芭芭雅嘎们的设定和命运,解构她们身上的文化附着物,并进一步将其引申为每一位活生生的女性。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节选了《芭芭雅嘎下了个蛋》第一部分,分享给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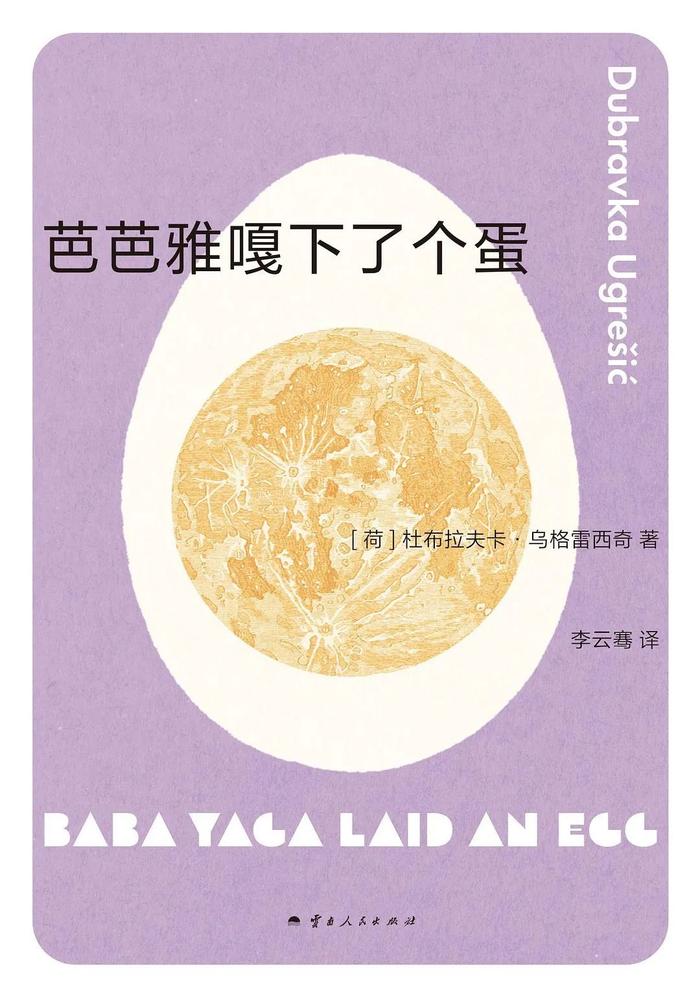
母亲的窗前绿荫如盖,树梢上挤满了鸟儿
夏天的新萨格勒布街区,空气中有鸟粪的味道,我母亲就住在这里。她公寓大楼前的树上,树叶间挤满了成千上万只鸟儿。是椋鸟,人们说。湿热的午后,雨水将至,这些鸟尤其喧闹。不时有位邻居会拿出气枪乱射一通,将它们赶走。密密麻麻的鸟儿成群结队地飞向高空,呈“之”字形上下翻飞,活像是在梳理天空的发丝。随后,伴着一阵歇斯底里的锐鸣,它们扎进茂密的绿叶间,如同一场夏天的雹暴。这里像雨林里一样吵,从早到晚都罩在一道声音做的帘幕里,仿佛外面有雨在一直敲。轻盈的羽毛乘着气流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妈妈拿出掸子,把羽毛扫起来,倒进垃圾桶,嘴上还念念有词。
“我的斑鸠不见了,”她叹了口气,“你还记得我的斑鸠吗?”
“记得。”我说。
我隐约记起她十分喜爱飞来她窗台的两只斑鸠。她讨厌鸽子。清晨,它们低沉的咕咕声令她非常恼火。
“那些讨厌得不能再讨厌的肥鸟!”她说,“你发现了吗,就连它们都不见了?”
“谁们?”
“鸽子!”
我没有发现,但的确,鸽子似乎都已经逃走了。
椋鸟让她心烦意乱,特别是夏天那股臭味,但她最后也习惯了。因为比起别人家,她的阳台至少是干净的。她指给我看阳台栏杆尽头的一小块污渍。
“在我的阳台上,只有这里会脏。看看柳比奇卡家的阳台吧!”
“看什么?”
“到处都结着鸟屎!”妈妈说,笑得像个小女孩。小孩子的秽语症,她显然是被屎这个字逗笑了。她十岁的孙子听到这个字也咧嘴笑了。
“像是在雨林里。”我说。
“确实像在雨林里。”她赞同。
“虽然现在到处都是雨林。”我说。
鸟群明显失控了,它们占领了整个城市,占据了公园、街道、灌木丛、长椅、露天餐厅、地铁站和火车站。似乎没有人发现这场入侵。喜鹊正在占领欧洲城市,据说是从俄罗斯飞来的,城市公园里的树枝都被它们压弯了。鸽子、海鸥和椋鸟飞掠过天空。笨重的黑乌鸦,喙张得像晾衣夹,一瘸一拐走在绿色的城市草坪上。绿色长尾鹦鹉逃出家庭鸟笼,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里大量繁衍:成群的鹦鹉低低飞过,像碧色纸龙一般染绿了整片天空。阿姆斯特丹的河道则被大白鹅占领了,它们从埃及飞来,盘桓休息了一会儿,便留下了。麻雀已经胆大到直接从人们的手中夺走三明治,还要在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上厚颜无耻地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我家所在的柏林达勒姆区是柏林最美丽、最绿意盎然的街区之一,短租公寓的窗户已成为附近鸟儿最爱的粪便存放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放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就只能每天辛苦擦洗被溅花的窗户。
你还记得我的斑鸠吗?
她点点头,但好像完全没有在听。
该地区的椋鸟入侵大致始于三年前,妈妈刚病倒的时候。医生诊断书上的语句冗长、骇人,而且丑陋(那真是一份丑陋的诊断),所以她才会选择用病倒这个词(我病倒之后,一切都变了!)。比较勇敢的时候,她也会用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额头,说:
“都怪我这里的蜘蛛网。”
她说的蜘蛛网是脑转移瘤,发生在她的乳腺癌被及时发现并成功治愈的十七年后。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历经一系列放疗,终于渐渐康复。后来她定期去复查,其他方面多少都还算正常,自那以后并无大事发生。蜘蛛网潜伏在大脑中一个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后来,她与之和解了,习惯并接受了它,就像接受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在过去的三年里,她的人生故事被压缩成一小沓出院单、医学报告、放射学图表,外加一堆脑部核磁共振和CT报告。扫描图像上能看到她轻微前倾的脊椎,上面连着可爱匀称的头骨,还有面部清晰的轮廓,熟睡一般低垂的眼睑,奇异的帽子般展覆的脑膜,以及浮在她唇边的一抹隐约的微笑。
“这张让人觉得我脑子里像是在下雪。”她指着CT影像说。
窗下的树,绿荫如盖,高大葱茏,一直长到与妈妈六楼的公寓齐平。成千上万的鸟儿在叶片间攒动。依偎在夏日炎热的黑暗里,我们,居民和鸟儿,呼出的气息在空中蒸发。不计其数的心脏,人类的和鸟类的,在黑夜中以不同的节律跳动。发白的羽毛乘着阵阵气流飘进敞开的窗户,像降落伞一样飘向地面。
我的词都散了
“把那个什么递给我……”
“什么?”
“那个涂在面包上的。”
“人造黄油?”
“不是。”
“黄油?”
“你明知道我好多年不吃黄油了!”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皱起眉头,因自己的无能而越来越恼怒,因此她立刻狡猾地切换到攻击模式。
“什么样的女儿会不记得抹在面包上的东西叫什么!”
“抹?奶酪酱?”
“就是它,白色的那种。”她气呼呼地说,仿佛她已经下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
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她很生气,她真想跺脚,用拳头捶桌子,大喊大叫。但她只是僵在那里,愤怒在她内心涌动,格外轻快鲜活。面对一堆词语,她只得停下来,就像面对着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
“把饼干给我,下体那种。”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纤体饼干。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她用更熟悉的下体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于是,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把耳机给我,我要给雅沃尔卡打电话。”
“你是说手机吗?”
“对。”
“你真要打给雅沃尔卡吗?”
“不,怎么会呢,我干吗给她打电话?!”
雅沃尔卡是她多年前认识的人,谁知道她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名字。
“你想说的是卡娅,对吗?”
“对呀,我说我想给卡娅打电话,不是吗?”她哼了一声。
我能听懂她的话。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会这样描述它: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这个任务很简单:指的是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
之后,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小可爱、小可心、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就连人名,包括我的名字前面,也会加上这些尴尬的昵称。它们就像磁铁一样,果然,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她最贴身的东西(我的甜心睡衣,我可爱的小毛巾,那个松软的小枕头,我的小瓶子,那双舒服的小拖鞋)。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
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语言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遵循着一条不一样的路径。
或许这样一来,她就没那么寂寞了。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没那么可怕了。除了这些小词,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蹦出来一些大词,像弹簧一样: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在她眼中,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他是个大——块——头!)。其实,是她变小了,世界就显得更大了。
她用新的、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她的嗓音有些嘶哑,声调有些傲慢,是一种要求听众绝对尊重的语调。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
还有一个变化。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冰箱,去浴室,按照某种规律的节奏,嗯嗯嗯,或者呜呼呼,呜呼呼。
“你在跟谁讲话?”我问。
“没有谁,就我自己。我在和自己讲话。”她回答。
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为了驱散恐惧,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
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她忘记了太多东西,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无论亲疏远近,朋友的朋友的死,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
“出事了。”
“怎么了?”
“我担心说了会吓到你。”
“说吧。”
“韦斯娜太太过世了。”
“哪个韦斯娜?”
“你认识的那个韦斯娜太太!住在二楼的?”
“不认识,我都没见过她。”
“失去儿子的那个,有印象吗?”
“没有。”
“电梯里碰见总是笑眯眯的那个?”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了。”
“就是这几个月的事儿。”她说着,合上了脑海中韦斯娜太太的小档案。
她的邻居、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她波澜不惊。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然而,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她却避而不谈。密友近期去世后,她一直缄默不语。
“她已经那么老了。”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
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T恤,这样的T恤她有两件。我们叫出租车时,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再叫一辆吧。我才不想上这辆呢!)。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她姐姐的、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换成她孙辈的、我弟弟弟妹的和我的照片,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
“我不喜欢死人,”她告诉我,“我想跟活人待在一起。”
她对逝者的态度也变了。在此之前,每个人在她的记忆中各有其一席之地,一切都井井有条,如同在一本家庭相册里。现在相册散了架,照片散落一地。她不再提起过世的妹妹,反而突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她的父亲。父亲永远在读书,还经常带书回家,父亲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她曾亲手把父亲送上神坛,如今又亲手把他拉了下来,关于父亲的记忆被她体会过的最彻骨的心寒永久地玷污了,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也绝对不会原谅。
然而,她给出的理由与谈起这件事时的痛苦并不相称,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有一对夫妇是外公外婆的好友。外婆去世后,他们一直照应着外公,特别是那位妻子,也是外婆的朋友,对外公十分照顾。有一次,我妈妈偶然目睹了外公和这个女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一幕,外公在亲吻她的手。
“我觉得很恶心,妈妈当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
外婆不太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照顾好我丈夫,照顾好我丈夫!这种可悲的恳求,是被妈妈塞进奄奄一息的外婆嘴里的。
与恶心的吻手画面粘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画面,妈妈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她上次回瓦尔纳时,外公请求妈妈带他一起走,但是她——被我父亲绵延的病情、临终的剧痛和最后的离世折磨得心力交瘁——惧怕责任的重担,拒绝了他。外公被遗弃在瓦尔纳附近的一家养老院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把我送他的小毛巾卷起来,夹在胳膊下面,转身进了门。”她这样向我描述他们的最后一面。
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
听上去,她是把一条毛巾夹带进了最后那一幕里。每年夏天,我们去看望妈妈的保加利亚亲戚时,总会带着一堆礼物。她不仅喜欢送礼物,还喜欢自己送礼物时的样子:她回到阔别已久的瓦尔纳,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就像一位善良的仙女。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与自己父亲告别的画面中加上一条小毛巾,仿佛她在用那条毛巾鞭打自己,仿佛夹在他胳膊下的毛巾是人类衰败时最恐怖的意象。衰败就发生在她眼前,她却袖手旁观,没想着要阻止,或者至少减缓一下它的颓势。她没有作出那真正的壮举,即经过漫长痛苦的官僚程序,还得不到确定的结果。相反,她塞给了外公——一条毛巾!
贬低死者是她最近才出现的需要。她的指责并不严重,全是零碎的细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很有可能是她当场编造出来吸引我注意力的,仿佛吐露了一个从未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也许逝者的形象现在由她掌握这一事实会让她感到满足。有时她回忆起故去的朋友,就像刚刚决定在学校记录上把他们的成绩降一档,她会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从来都不待见他;也从来没怎么喜欢过她;我对他们印象都不好;她一直是个小气鬼;不,他们都不是好人。
有一两次,她甚至想抹黑我父亲的形象,这位她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将他留在了他死后她为他建起的神坛上。
“你不是真的爱他爱到发狂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但我确实爱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安静。”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爸爸确实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我记忆中的外公也是位沉静的人。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仅都安静,还都是妈妈见过的最诚实的人。
也许通过对逝者偶尔的亵渎,她可以消除自己本该做某些事却没有做的负罪感。她用严苛的审判来掩饰自己对最亲近的人不够尽心尽力的愧疚。她似乎只是害怕多关心别人一点。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她就像畏惧死亡一样畏惧生活。所以她才会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固守着自己渺小而倔强的坐标,面对那些对她来说太过刺激的场面和情景,她选择闭上眼睛。
洋葱一定要炒熟。健康是第一要紧的。撒谎的人是最坏的。老年是可怕的灾难。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煮羽衣甘蓝一定要倒掉第一道水。
也许她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我没有在意。现在,一切都变小了。她的心脏萎缩了。她的血管变细了。她的步子变小了。她的词汇量缩小了。生活也越缩越窄。她以特别的分量说出这些老套的话。我想,这些老生常谈让她觉得一切都还好,世界各安其所,让她觉得她仍然掌控着一切,仍然有决定权。她挥舞着她那老一套,仿佛它们是无形的印章,她把它们盖得到处都是,急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她的头脑仍在运转,双腿也还合用,她能走路,诚然,是在助步器的帮助下,但是她毕竟能够行走,她仍然知道豆子最适合拌进沙拉吃、老年是可怕的灾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