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的布鲁克林时代:那里为他提供了一生的精神食粮
在美国,没有一个城市像布鲁克林那样戏剧性地见证了市场革命的影响。一八一〇年,它还只是一个仅有四千多人的普通村庄,毫不起眼,到了一八五五年,它已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人口竟然超过了二十万。即使在美国显著增长的时期,布鲁克林发展速度之快也让人瞩目。惠特曼在布鲁克林生活了二十八年,那儿是他生活最久的地方,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孕育了我们的诗人。位于安详的长岛乡间和迅速扩张的曼哈顿市区之间,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这对诗人来说意义极其重大。“我在布鲁克林出生长大,”他告诉特劳贝尔,“在那儿很多很多年,品尝到了它那亲切的生活。”一八九一年,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生日庆祝会上,他告诉他的追随者说,他的“成长和工作的日子”就是“纽约和布鲁克林,在那儿做的各种尝试……纽约和布鲁克林的真实生活,那是所有其他一切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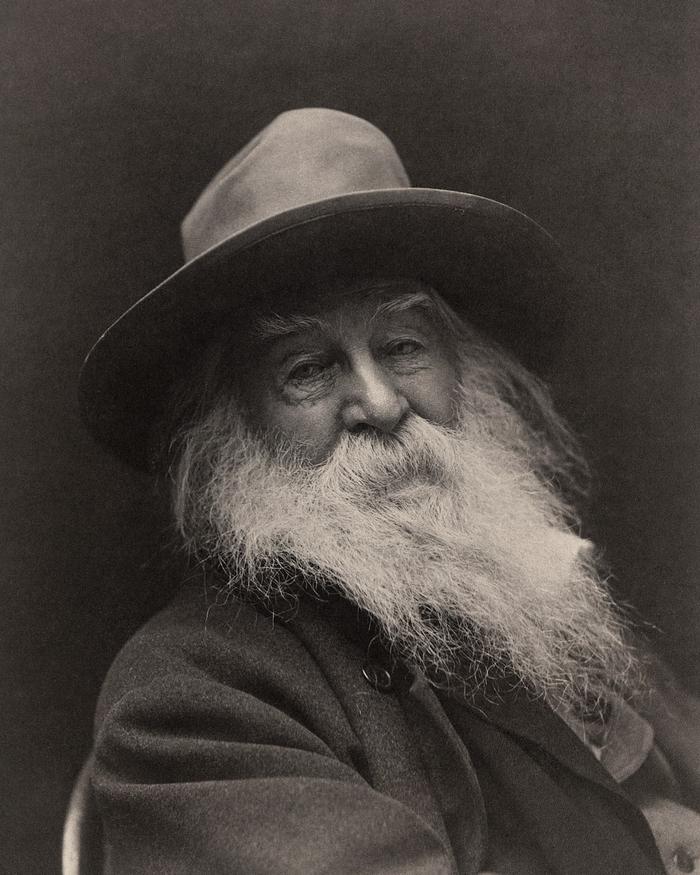
重温他在布鲁克林的早期生活,我们发现,那儿不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影响的交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十六岁那年,他离开布鲁克林去长岛做了一段时间的教书匠,那时,他已经接触到基本的宗教、文学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将为他提供一生的精神食粮,也是他那文化上极具代表性的诗歌的素材。
一八五七年,《草叶集》第二版问世不久,惠特曼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带着深深的情怀回首他在布鲁克林的童年时光。他写道:“那些岁月,那些活动,对于现代布鲁克林这些忙碌不堪、拥挤的人潮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三十年的时间已经改变了“布鲁克林的方方面面”。
他说得很对。当时的布鲁克林有一种粗犷的朴素美,只是在随后的扩张过程中很快就被摧毁了。总的来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生活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这一点有时我们大家都忘掉了。生活用水要用街道水泵抽出来,再用木桶运送回家。泔水和垃圾都是倾倒进大街的臭水沟。
既没有集中供暖,大厅也没有炉火取暖,每个房间都要生炉子。到了一八二九年铁路才开通;一八三〇年才有了胶鞋和硫磺火柴,一八三一年出现了有轨电车,一八三五年报业才开始使用蒸汽印刷机,一八三九年冰箱和达盖尔银版照相技术才开始流行。终其一生,惠特曼兴致勃勃地见证了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新鲜玩意,都是他小时候没有见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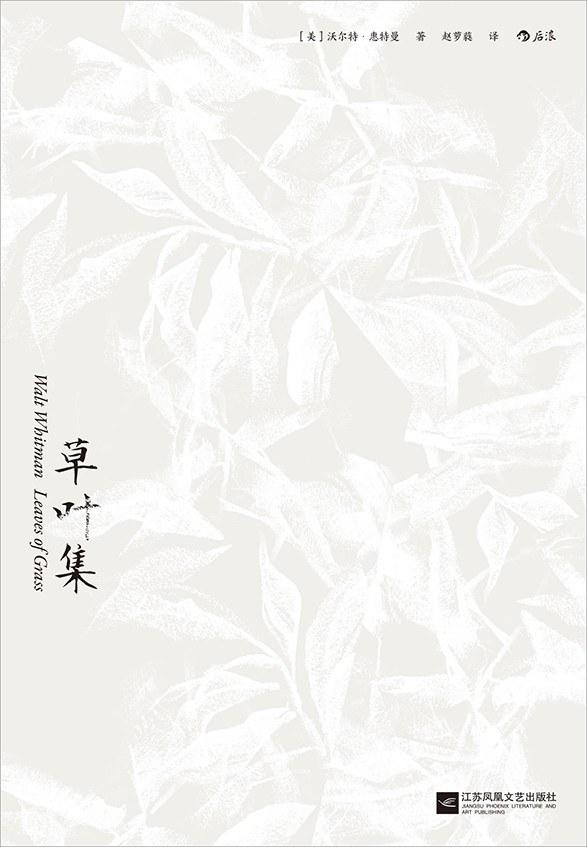
早期布鲁克林的原始风貌尤为引人注意,那是因为它后来变成了一个拥挤的城市,开始朝周围蔓延。甚至当时曼哈顿的部分地区都是乡下。一八二年,纽约最高的建筑物也只有四层楼高,人们可以站在布鲁克林高地(当时是三叶草山),目光穿过曼哈顿,越过哈德逊河一直望到遥远的新泽西海岸。到了一八五〇年,曼哈顿才开始向外扩展,最远也只是扩展到三十四号大街,再远处就是农场及乡村的旷野;甚至连二十三号大街也有乡村的感觉,到处都有风儿吹落的苹果花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翻滚着。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布鲁克林充满了乡村小镇的特色。正如惠特曼在六十年代回忆的那样,“布鲁克林极具乡村特色,与现在的样子比起来,它简直就是一个大农场、大花园”。公共马路上到处都是猪和鸡,整天都在大街上的垃圾中觅食,当时根本没有垃圾处理系统。街道大多是土路,也没有人行道,冬天泥泞不堪,夏天尘土飞扬。一八二八年富尔顿大街才有了煤气路灯,但是很久以后才推广使用,所以那时晚上出门人们不得不打着灯笼,小心翼翼地行走。卫生条件极差,霍乱流行时有发生。当时没有消防泵,巨大的火灾时有发生,吞噬大片的房屋和棚屋。除了教堂和建于一八二五年的“学徒图书馆”外,当地没有什么大型建筑。古老的树木遮蔽着村庄街道,向东延伸,没多远就全成了乡间小路,通往早期荷兰殖民者后代还在经营的边远农场。
在惠特曼心目中,长岛意味着自然,曼哈顿代表的是商业和文化,而布鲁克林区则是两者完美的结合。他写道,长岛“肥沃,美丽,水源充沛,木材充足;而曼哈顿是到处是岩石,寸草不生,一片荒凉,除了可用于商业用途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优势,而商人的野心可以征服世界”。布鲁克林是两者中间的通道,是个黄金地带。用他的话说,“的确,我怀疑世界上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城市能比布鲁克林更美好,或是更实用”。
坐渡轮只要十五分钟就能到达纽约:布鲁克林的富尔顿大街有一块巨大的路牌,就在身材健壮、热情好客的科·唐宁开办的酒馆、客栈外面,上面是许多遥远的长岛乡镇的名字,一半是印第安语的,另一半是英语的。对惠特曼来说这一直都是个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记忆。
诗人常用的一个隐喻是布鲁克林具有很好的联结作用:布鲁克林联结了美国的不同地区,联结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联结了过去和未来。这一联结隐喻的部分原因源于他早年在布鲁克林的经历。那是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五年,他最早生活在布鲁克林,那时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虽然处于暂时休战时期,但是二者之间的局势很不稳定,多年来,一直酝酿着深深的敌意。
直到一八一六年,曼哈顿还在牢牢地控制着东江渡轮和布鲁克林区海岸,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皇家特权。布鲁克林当年经过合并成为一个村庄时,虽然赢得了其中的一些权利,但对这座城市的统治仍然保留着怨恨,由谁控制渡口向来是个棘手的问题。纽约一直想兼并布鲁克林,但布鲁克林却顽强地要保持独立,并最终于一八三四年四月被特许成为一个城市。直到一八九八年布鲁克林才与纽约合并——这种延误主要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宿怨造成的。布鲁克林的支持者把纽约看作罪恶的渊薮,而曼哈顿的狂热支持者则认为布鲁克林粗鄙不堪。一位布鲁克林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纽约和布鲁克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是目标、兴趣还是感情上都格格不入——甚至连表面上相似的东西都没有,唯一相似的就是在它们之间的水流。”
它们之间的水流。惠特曼在诗作《横过布鲁克林渡口》中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共同点,该诗从东江发展的角度描绘了两座城市。在他的新闻报道中,他经常支持布鲁克林,强调自己家乡城市的宜人之处,并称纽约为“河对岸的蛾摩拉”。他甚至提议把长岛变成以布鲁克林为首都的巴门诺克州。尽管如此,他始终都能意识到,比起布鲁克林来,曼哈顿在文化和商业上优势明显,从小他就定期乘坐渡船来到这个城市:他完全沉浸在这两个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汲取了这两个城市的优点,忽略了他所看到的最坏的现象,成为第一位伟大的城市诗人,并在自己的诗歌中从审美的角度使得两者之间达到了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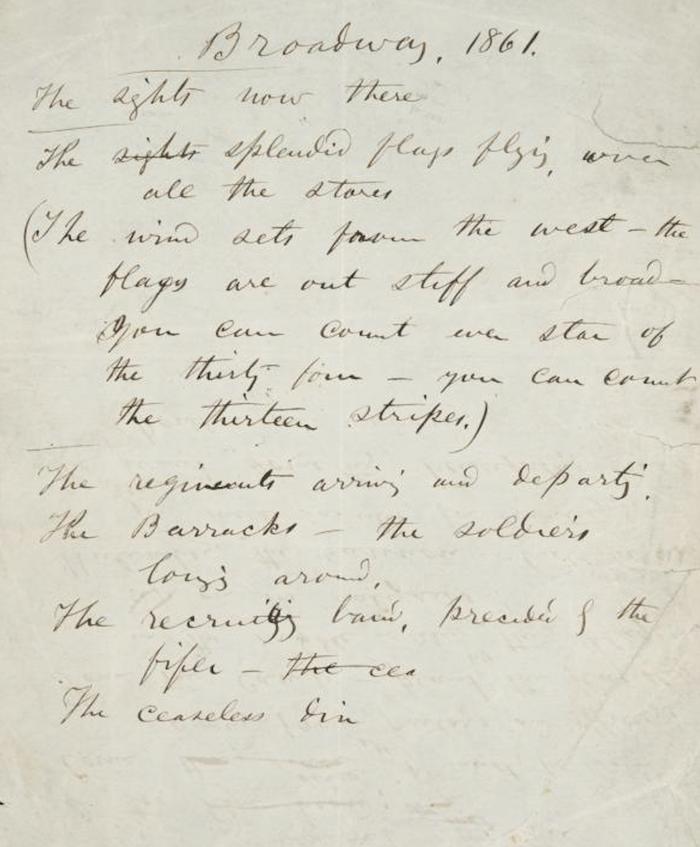
在他看来,布鲁克林本身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联结的象征,正是因此他才得以在其诗作中扮演起联结者和平衡者的角色。这在他少年时代尤为如此。虽然一八二五年伊利运河的开通加快了布鲁克林的商业化,但在早期,它却具有那种美国小镇的风情。现在许多高大建筑耸立的场地当时仍然是开阔的田野,邻居的孩子们聚集在那里玩耍。惠特曼在布鲁克林的田野里养成了对棒球的终生热爱。每逢周六,他都会和其他男孩一起兴致勃勃地去打棒球,那种早期的棒球玩法与现在不同,看上去有些奇怪,其中一名跑垒者被外野手投出的球击中后便被淘汰出局,这种玩法会使球员全身擦伤。对于球棒,大家可使用随便捡起的扁平或圆形的棒子;至于球,自己动手,用旧袜子纱线和手套皮包上零碎软木或橡胶就可以了。打小时候起,沃尔特就擅长棒球,他后来称之为“美国的游戏:它有美国特色的情调,接球,跑开,扔出去”。
当时流行着一种亲密和友爱的氛围,甚至连公众的庆典和节日也都沾染了这种特性。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节日庆典开始由专业人士操纵变成大众化的宏伟场面,惠特曼如果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大吃一惊。他最著名的诗行之——“我礼拜我自身”——在一个层面上,可以作为他的一种恢复庆典的尝试,使那种冷酷地被操纵的大众庆典回归到个人的、真心的庆典本质。也就是伴随他成长的布鲁克林那种个人庆祝活动。后来他带着怀旧的情调回忆道:“那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有时是主日学校举行的,有时是由正规的教育机构操办,有时是这样或那样的周年纪念日。”在元旦那天,人们都是尽可能地多拜访一些朋友。街道上来来往往,到处都是走亲访友的人们。复活节期间人们特别活跃:在长岛的非洲裔美国人欢聚一堂,欢度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又叫作圣神降临周,他们在长岛喝酒、跳舞、恶作剧;他们的笑声响彻整个村庄。白人们聚集在街上庆祝,大家会一起砸鸡蛋。
在惠特曼的记忆中,那时最典型的庆典是拉法耶特侯爵在一八二五年七月四日访问布鲁克林那一次。那是这位革命战争英雄的美国胜利巡回之旅,他能来到布鲁克林区那真是一个难忘的事件。他乘坐一辆黄色老式四马马车,穿过小镇,来到克兰伯里街和亨利街的拐角,在那里他为学徒图书馆大楼主持了奠基仪式。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烟花,也没有礼炮,只有沿街列队站立人群的那种真情流露,整个庆祝活动自然而然、真诚实在。惠特曼回忆说,整件事“都显得朴素,自然,没有浮夸轻浮或哗众取宠,而且具有某种庄严肃穆的古代庆典氛围”;他强调说,“这与现代社会如此盛大的人群庆典完全不同”。有两次他回忆到这次事件,都说当时拉法耶特把村里的几个孩子抱在怀里,其中就有六岁的惠特曼。拉法耶特还吻了他的脸。是惠特曼的想象吗?很有可能,但它却真实地显示了这些记忆中的早期庆典对惠特曼来说是多么亲切。
如果说布鲁克林的节日充满了人情味,那么它的公共教育却往往是没有人情味的。直到一八二七年,布鲁克林也还只有一所公立学校,即布鲁克林区第一小学,一八一六年建于康科德和亚当斯大街。这是惠特曼从一八二五年(可能更早)到一八三〇年读书的地方,那时候家中生活拮据,他只好辍学去打工。这所学校名声很差,据说只是“为了给读书人一碗饭吃”。尽管如此,沃尔特家还是比许多人过得要好一些;在布鲁克林,五岁到十五岁孩子中有四分之一根本上不起学。尽管一八二七年又有了第二所学校,但即使在那时,村里也只有两名教师,而学生却有两百多名。像当时大多数学校一样,布鲁克林的学校也是按照英国贵格会教友约瑟夫·兰开斯特建立的那种僵化的体制来运营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位教师下面有好多学生干部,帮助管理庞大的班级。
教师高高在上,行使专制的权利。学习都是死记硬背。学校从上午九点开始上课,先读圣经,进行道德教育。小学生要学习听写、算术、拼写、地理和作文。高年级要学语法、几何学、三角学、历史和许多科学课程,包括动物学、生理学、天文学、矿物学和博物学。惠特曼是十一岁辍学的,可能接触过一些这些高年级课程。体罚是兰开斯特教育体系的方法之一。毫无疑问,惠特曼上学时看到过体罚学生,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谴责学校鞭笞学生行为的。虽然他从未写过他对学校的感情,但我们可以猜到他上学时过得很不舒服。在他的老师哈洛克的记忆中,惠特曼是“一个大个子,脾气挺好,笨手笨脚的,是个外表很邋遢的小伙子”。得知沃尔特已成名后,他说:“我们永远不要对任何学生失望。”就像哈佛大学的爱默生和鲍登学院的霍桑一样,当时在区第一小学读书时的惠特曼显然只是个平庸的学生。他早期接受的是僵化的兰开斯特式教育,很不满意,正因如此,后来他转而寻求其他更为温和的教育理论,并将其融入他的诗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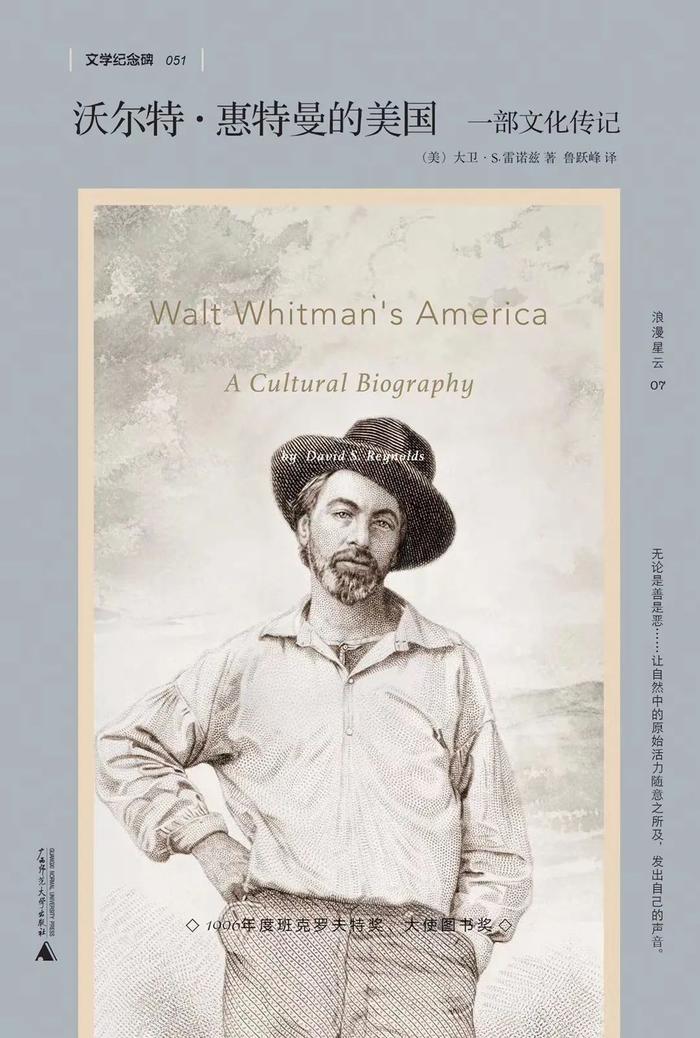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美]大卫·S.雷诺兹著,鲁跃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3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