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消费主义”到“照顾自己”:药物成瘾者难以完成的拯救
据海外网6月4日援引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最新调查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自述有认识的亲友因滥用阿片类止痛药品而死亡。这篇报告刊登于《美国医学会网络》(JAMANetwork)。
滥用阿片类药品、药物上瘾一直是美国青少年的最大社会病症之一。在2023年去世的演员、《老友记》中钱德勒饰演者马修·派瑞也曾备受药物上瘾的折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样或那样的医疗机构度过,为了活下去,他把自己熬成了一个职业病人。去世前,他不止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呼吸骤停,昏过去,或者换个词——痛死过去——有一次还断了肋骨。他为酒精和药物上瘾付出了超出他本人能承受的代价,最终因此失去了生命。

《老友记》(Friends)第十季(2003)剧照。
借用医学人类学者托德·迈耶斯(ToddMeyers)的话来提问:一个人依赖让自己身处险境的药物——究竟是因为在寻欢作乐中迷失了自我,抑或根本就是对自我的漠视?
这恐怕是每个人听到有人药物上瘾后,都会有的疑问。如果说是他们故意放纵,可成瘾的后果却又是他们知道的,如果说只是某次意外上了瘾,成瘾者的阶层和家庭背景却又呈现出某些特征,表明那似乎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
大多数成瘾者“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治疗机构被治疗。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托德·迈耶斯《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以下简称《诊所在别处》)一书,内容为作者讲述他与青少年劳拉之间的互动,他对机构治疗内外都作了反思(并非否定临床试验),也让读者看到治疗机构无法观察到的复杂性。他的这一判断也适合其他治疗场景,人、身体、心理和精神都有复杂的一面,甚至是不可被观察的。人们唯有进入当事人生活,通过不断的对话、体验才可能实现部分了解。
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文。
原文作者|[美]托德·迈耶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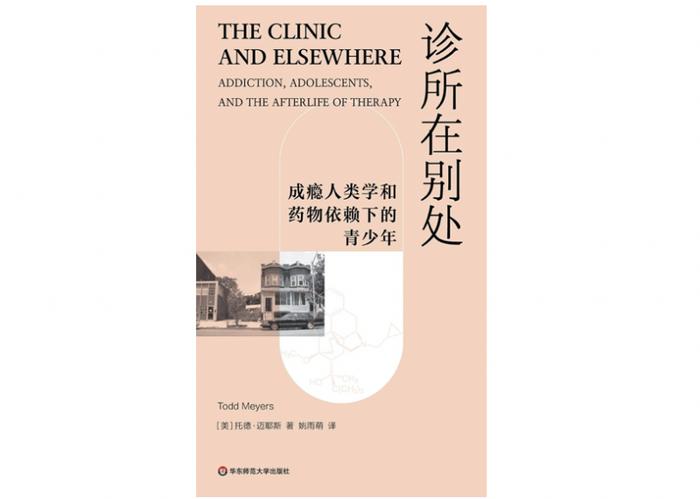
《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美]托德·迈耶斯著,姚雨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劳拉:一个故事的开头
研究一开始,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就把劳拉介绍给我认识了。
相比于调查中的其他青少年,劳拉的人生经历说不上坎坷,家庭环境也不复杂;相比于其他人的父母,她的父母也不是“穷忙族”,反倒颇有几分中产阶级的遗韵。但是,劳拉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史却与治疗中心里的其他青少年无异。她从14岁开始就一直在滥用处方药,至今已经有两年了,最开始是和男朋友一起嗑药,然后就一直没断过,直到有一天父母“不顾她的意愿”、“强迫”她去接受治疗——劳拉当时“大喊大叫、胡踢乱踹”(引自她妈妈的话)。
与劳拉见面之前,她已经入院接受过一次治疗了。两次入院的间隙,她在巴尔的摩看了私人医生,医生给她开了舒倍生。但是从劳拉的描述看,治疗似乎并不成功:
有些事你得明白,可能也只是我的看法啦,我觉得没理由吃几颗药就能包治百病。药本身才是问题所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吃起药来很有一套的。(大笑)我服药(舒倍生),但我也嗑药(别的药),那我就得吃更多的丁丙诺啡,然后医生就会说:“你还在嗑药!为什么啊?治疗不是有效果吗?”我就说:“我干嘛不嗑?”每当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为所欲为。那个医生人挺好的,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问劳拉怎么看没法相信人们会遵医嘱服药这件事——这也是我和她在治疗中心对话的主题。
梅达德:你觉得只是舒倍生比较特别吗?还是说换了别的药,人们也一样?
劳拉:不,就只是这个药吧。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所有的药都一样啦。人们也没有按医嘱服用抗生素啊,不然为啥我父母的橱子里有十来个只吃了一半的处方药瓶?你觉得自己好了,就停药了,就是这么回事。不管别人多恼火,我吃药的时候,自己的感受才最紧要。
梅达德:所以你在服用舒倍生的时候,也是觉得好了就停药了?
劳拉:不,我还是继续服药的。虽然吃起来像是在舌头下面塞了个硬币,但我还是坚持服药的。我没有理由停药呀,但我也没有理由停止嗑别的药啊。
我在和劳拉的谈话中发现了奇怪的一点,相比于住院治疗,劳拉反倒更容易在看私人医生的时候重蹈滥用处方药的覆辙,不过这不是重点。她坚持服用舒倍生,打算继续接受住院治疗,并且在住院期间就不会嗑其他药了。“我是这里的一部分。”她对我说道,但究竟是“哪一部分”,她却说不清了。

“滥用药物”常见于美国底层社会叙事。图为由J.D.万斯同名畅销书改编电影《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Elegy,2020)剧照。
随着与劳拉在治疗中心的聊天越发深入,我也越发清晰地了解到她和里面年轻人之间的联系。待了几周后,劳拉的行为举止都发生了变化,她掌握了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开始用一些诸如“毒品的选择”和“我的滥用史”之类的术语,就像参加了无数次小组治疗后的青少年一样,这些短语轻轻松松地从她嘴里蹦出来。等到转去强化门诊治疗的时候,劳拉为离别分外感伤。我看着她与工作人员以及很多玩得好的青少年一一拥抱告别,能离开这儿本是充满希望的一件事,但对劳拉而言,却满怀悲伤。
劳拉来看门诊的时候,我便借机跟她聊了聊,她说还是很想回去,想再住院。我问起她对未来有何打算(比如上学、工作或是什么时候去学车),她却茫然不知。之后,她再也没来过门诊,我问她妈妈发生了什么,她妈妈说劳拉去找原来的那位私人医生治疗了。
更偏爱治疗中心的理由
在我结束治疗中心调查的前两天,劳拉又被收治入院了,她看起来倒没有受戒断的煎熬,也不是嗑嗨后神志恍惚的样子,反倒是满心欢愉,如果真要说有什么不好,大概就是有些疲惫罢了。我问她为什么回来,她的回答很简单:“我想这儿了呗!”劳拉在治疗中心的时候,可是个模范病人。“她超棒的,”其中一位社工跟我说,“但我想不通她为啥回来找我们,如果她出去后能继续保持,那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在治疗中心里,劳拉依赖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可是一旦生活中没有了这种结构或是什么其他可以依赖的东西,她就崩溃了。劳拉告诉我说:“当我回到这里,实实在在地身处其中的时候,跟我在外面的感受全然不同,这跟治疗没有关系。”
劳拉很期待住院,她妈妈也察觉到了这点。“她特别喜欢这儿,但我们超级讨厌这儿。”劳拉第二次入院后,在一次家访中她妈妈说:“我们觉得好像把她遗弃在这儿了。”爸爸也在一旁拼命点头。她继续说道:
我们希望她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也试着在家里给她一些空间,我们对她真的没有什么要求了。她可以去上学啊,去找朋友玩啊,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对她很好了。而且,她在学校也很受欢迎的。我们不喜欢治疗中心里的风气。她跟我说这里其他孩子的故事,听得我简直头皮发麻,什么滥交啦、强奸啦,还有艾滋病——这可不是我们劳拉的生活——可她却对这些孩子产生了认同感。我知道他们也是好孩子,哎呀,但还是有些不放心啦,我们真的尽心尽力了,连手心都没有打过她。(劳拉的父亲插了一句:“天哪,那怎么成。”)他爸爸和我从来都没碰过毒品,我就是生病了也不吃药,是药三分毒啊,我真想问问她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劳拉的父母坚称他们没有想要“控制”的意思,对他们而言只是“引导”。

以药物成瘾为背景的电影《成瘾剂量》(Dopesick,2021)剧照。
但是劳拉说起和父母的关系时,却说自己“有点想搞事情”。劳拉希望(在家外面)能有个地儿让她自己做“糟糕的决定”。尽管住院治疗中心里事无巨细的管理规定常常因为太过严苛而让里面的年轻人产生逆反心理,但是劳拉恰恰相反,反倒觉得在治疗中心里可以“独立生活”,因为这里有家中体会不到的自由。治疗中心的住院部,虽然“有很多条条框框”,但也有让劳拉像个“大人”一样生活的空间,她在这里可以自由决定“搞事或者不搞事”。劳拉将家(以及去私人医生那里就诊)视为自己没有选择、只能做出糟糕决定的地方。
照护的逻辑
安玛丽·摩尔在《照护的逻辑:比病患选择更重要的事》中将病人的自主性和对健康的追求视为照护的逻辑和选择的逻辑之间的较量。对于个人选择是治疗的前提一说,摩尔认为更重要的是,在看病过程中,人们需要倾听个体的声音。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医疗消费主义的大旗下,“选择”等同于对“美好生活”的模糊渴望。她在书中写道:“在照护过程中,我们要召唤的,是我们的心智,而非欲望。”然而,鉴于疾病的现实,照护也并不是全然理性的:“我们的欲望或许不是理性的,但是就照护的逻辑来说,我们的心智也并不是理性的,相反,我们的心智充满了缝隙、矛盾和执念。”摩尔对照护和选择的区分将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使得照护和照顾(caregiving)的行为和条件陷入非理性的境地,事实上,如此境地正是我们的共谋(complicit)。
在摩尔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将自我从集体中分离出来的挣扎。此外,她还提出了关于自我照护概念的局限和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意思又很难回答。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只需要看亚瑟·弗兰克(ArthurFrank)试图调和“照顾好自己”所必要的隐瞒与在病中对“坦白”或“叙述”的渴望即可。在《性史》第三卷中,我们看到米歇尔·福柯提出了“关注自我”的概念。“自我照护”、教化或“照顾自己”,都重申了个体的重要性——还有一件有争议的事,即治疗过程中的活动(治疗阿片依赖)如何模糊了自我照护和与他人伦理关系中的照护所必需的条件——这一点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斯坦利·卡维尔、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均有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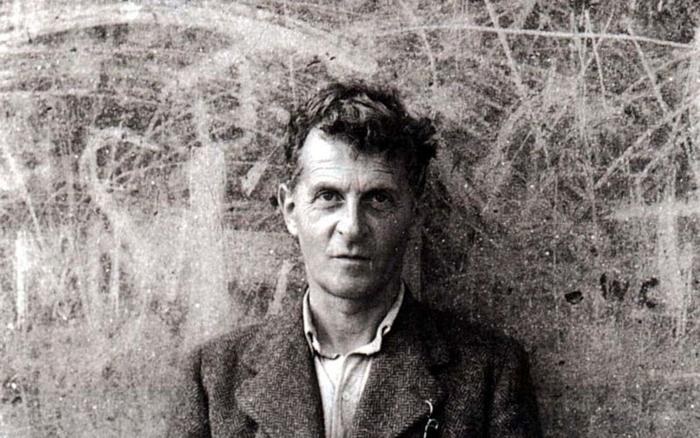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哲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此外,这些关系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治疗实践和暗中照护他人的行为来表达的呢?卡罗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的“照护伦理学”(ethicsofcare)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解决方案——一种不囿于政治经济学或正义的抽象原则。吉利根在作品中重申了照护在面向他人的社会活动中的价值,同时也说明了人类关系中的复杂结构——这也是米歇尔·福柯所关注的问题。重新定义依赖关系的尝试是“照护伦理学”的起点,或者至少是在政治人类学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正义理论的起点,通过这样的尝试来揭示道德主体的构成关系。
照护,作为医疗干预的结果,必须考虑对象(药)以及使对象成为治疗载体(心理治疗、医嘱等)的行为。近年来,席琳·勒弗夫认为医疗技术及其重要性可以说涵盖了照护的特征。像是“照护某人”这样的表述所承载的意义看似非常接近治疗干预的实际理想,有趣的是,这里的照护和治疗,在理论上(实际上)已经变得难以区分——这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需要我们反复追问关于照护的问题以及治疗的问题。照护,似乎存在于某一事件或某一瞬间,又或是一系列使其可能发生的条件(制度性的、主体间性)中的某个地方,这也让提供照护成为可能。这些条件必须包括受限制的能动性、患病的特殊问题、生物医学环境和一套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使照护的逻辑和治疗管理的逻辑紧密结合,这些条件是作为治疗行动者的自我(但是治疗方向可能严重偏离轨道)和治疗学之间的一种联结——同时也联结了临床环境与进入其中的病人。
治疗方式的分歧
《药物成瘾治疗法》允许医生在高度受控的临床医学环境之外开具丁丙诺啡的处方,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治疗空间。2002年10月,随着利洁时制药公司开发的药物获批,在办公室环境治疗阿片成瘾成为现实。对丁丙诺啡相关条例的调整以及FDA对新药的批准标志着制药公司的胜利,同时也有助于倡导更全面的成瘾治疗。
然而,随着乐观情绪的增长,人们也开始担忧阿片类处方药的滥用以及新的用药群体——正在使用处方类止痛药的年轻人以及本没有阿片类药物滥用史,但因为慢性病或术后疼痛开始依赖此类药物的老年人——的形成。

以药物成瘾为背景的电影《无痛杀手》(Painkiller,2023)剧照。
乍看之下,丁丙诺啡的故事和三十多年前的美沙酮的故事类似。和作为治疗阿片类药物依赖的特效药美沙酮一样,人们对丁丙诺啡的期待已逐渐变为对药物转用和滥用的忧虑(或者至少是有关的),但是,二者仍存在诸多差异。从药理学角度看,相比于美沙酮,丁丙诺啡的副作用小很多,患者较少出现呼吸窘迫的不良反应,这比以前的任何替代治疗都来得更加安全且更具治疗价值。然而,最大的区别在于治疗环境本身。与美沙酮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在高度受控的特定治疗环境之外获得丁丙诺啡,私人医师完成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一些简短的培训模块后,就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门诊开具丁丙诺啡的处方了。不必像之前那样,要把病人送到专门的成瘾治疗服务中心。
突然之间,开处方的医师能够根据个人判断来提供治疗,这种变换也扩展了临床意义。然而,准确来说,尽管有这样的变化,但丁丙诺啡似乎还是卡在这两种相悖的叙事之间:一种是“相同”——重新产生对个体风险和公众威胁的担忧;另一种是“不同”——试图确保新药及其治疗方式能让临床医生更有效地处理成瘾问题,这是一种怀有新希望的说法。这些观点不仅在公众与专业讨论中引起了回响,也引发了医生、家庭成员以及病人之间对治疗期望的讨论。
从高度受控的治疗环境转移到办公室门诊不仅改变了治疗的空间,也改变了“成瘾治疗”的概念。虽然药物治疗的广泛应用带来诸多益处,但是其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以及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距离也愈发明显。基于与医生在私人门诊以及专门的住院治疗环境中的交流,我发现,这种距离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社会经济方面(将负担得起私人治疗与负担不起的人分开),而在于医生、病人和家人彼此所想象的治疗方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尽管有些许经济负担,但劳拉的家庭还是付得起私人治疗的费用的。不过从劳拉父亲的说法中可见,说到底这不是钱的问题。劳拉的父亲曾是海湾战争的中士,战后去了职业学校,然后就在退伍军人管理局(VA)的医院里担任维修主管。“你想不到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回来的孩子要面对什么,”在对劳拉家访时他告诉我说,“那些沉迷毒品、不幸截肢、被绝望缠绕的人,哪怕我们曾并肩作战,现在也无法相互理解了。”劳拉的父亲十分担心战后回来的人们“迷失在体制中”的状态。“他们之前依赖军队,之后就依赖退伍军人管理局。我算走运的,未来还有盼头。但是这些孩子,我的天……”

以药物成瘾为背景的电影《成瘾剂量》(Dopesick,2021)剧照。
劳拉的父亲凭着一技之长让自己“拥有更好的未来”,这也直接影响到他想让劳拉远离住院治疗。“我看VA和这里(这个治疗中心)是同一个体制下的一部分,”他说,“要是就这么放弃她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与其说社会阶层或是社会经济条件在公共治疗与私人治疗之间制造了差距,不如说(对劳拉的父亲来说)需要与这些地方所承载的意义保持距离——这一方面与体制相关,另一方面与照护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承诺有关。
恐惧与承诺
用其他阿片类药物来治疗并不只是简单的替代而已,药代动力学特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阿片类药物的药理并非千篇一律,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临床上、社会上、政治上)被人们所接受。吗啡、美沙酮和海洛因的止痛功能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发挥过治疗价值。最新的例子应该是在欧洲某些地区,人们用海洛因作为阿片类药物滥用的替代疗法,此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由此可见理解治疗价值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药物在临床语境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并不足以平息社会对药物滥用的担忧,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历史的联想。即便在高度受控的治疗管理环境中,当人们将阿片类药物作为主要治疗手段时,也难免提心吊胆。然而,历史流变以及地方背景无法解释丁丙诺啡如何深刻影响了重建药物依赖治疗的概念,同时,无法与实际治疗方式调和的隐患也仍旧隐约存在着。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篇简短的文章称,丁丙诺啡获批用于办公室门诊治疗后,不会像美沙酮一样成为新的滥用药物。丁丙诺啡提供了一种药理学上“更精细”的替代疗法,但即便新疗法让更多的临床医生参与治疗,公众仍旧对大量阿片成瘾者目前没有接受治疗这一问题产生了公共卫生层面的担忧。在办公室门诊中,阿片成瘾者的临床表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正新鲜的是在这一环境中丁丙诺啡治疗成瘾的能力。
“能有这些药太重要了,你想不到药物依赖的问题有多严重,”一个在私立行为健康中心工作的年轻医生告诉我:
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是丁丙诺啡是个新事物,不是因为我们用它来治疗成瘾所以新鲜,而是因为一想到成瘾就必定会想到与之对抗的(药理)武器。现在我们有了新武器,那成瘾也不一样了,你懂我意思吗?至少对我而言,不可能只想到成瘾而不去想干涉的方法。
他接着解释办公室门诊治疗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方法”,就像正式的住院治疗中也没有一种固定的方法一样。
我的确采访了一百多个医师,大多是通过电话访谈。我发现他们除了都认为治疗是一个积极的转变,很难再有什么统一的看法。从一开始,各方就接受了可以在办公室门诊开具丁丙诺啡处方这件事,这与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尝试在基础医疗机构而非美沙酮诊所拿药治疗的事情全然不同。“这种比较简直无从下手好吗!”在巴尔的摩南部基础医疗机构为低收入人群服务的内科医生告诉我说:
我就是这个行动(推动在诊所开展美沙酮治疗)的一分子。我们自己作了繁文缛节的茧却缚住了自己(笑)。太糟了,不但一点没减少美沙酮的污名化,反倒加重了。我给二十多个病人用丁丙诺啡治疗,目前还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行政上倒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以药物成瘾为背景的电影《无痛杀手》(Painkiller,2023)剧照。
我想知道,人们只是把这两种治疗(住院治疗和办公室门诊)视为不同的工作方式,还是有着孰优孰劣一说。“是,也不是,”一位在住院治疗中心主治药物成瘾的精神病学家如此答道:
心理社会治疗是药物治疗的重要补充,但在两种治疗中所用的药物和剂量几乎没差别,监测方式也差不多。我们在研究中监督服药,但是一旦切换到门诊治疗,我们就会相信他们依然按着计划(处方)走,所以说在私人治疗中也都差不多。
然而,从临床医生个人的角度来看,很难回答这样的治疗有没有真的惠及新人群这一问题。巴尔的摩卫生委员约书亚·沙夫斯坦(JoshuaM.Sharfstein)博士力争通过2006年的《巴尔的摩丁丙诺啡倡议》来努力扩大治疗服务规模,使丁丙诺啡成为这座城市阿片成瘾的一线治疗药物。然而,这一倡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得找到有资格开处方的医生。医生在开具丁丙诺啡处方的时候,的确按要求完成了必要的报告,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在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中,丁丙诺啡在多大程度上被有组织地采用。公共与私人治疗环境外观的变化,以及谁在“观看”都成为临床医生以及新闻媒体挥之不去的担忧。与我交谈的医师在办公室门诊工作,却提出了与在住院治疗中心工作的医生相似的观点。但是对病人而言,体验过两种不同的治疗环境之后,其中的区别便凸显出来了。
照护的可见与不可见
“能回来我特别高兴,”劳拉回到住院治疗中心时跟我说道,“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回来的(微笑)。”在劳拉的案例中,不知道是不是她对治疗中心的好感使得她在其中的治疗比私人治疗更加“成功”。但我们必须得考虑治疗中心之外的世界对她的困扰,才能去确定背后的动机。人们假设办公室门诊其实与住院治疗的效果相当,或者说在这些环境中进行个人化的治疗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劳拉的案例却一再反驳了这一假设。“不管在哪儿,如果人们能够得到帮助,我就很高兴了,”一位治疗中心的临床医生这么跟我说,“拜托,我才不管是哪一种有用呢。”
在劳拉的例子中,有一系列复杂的对象和行动者在探寻“什么有效”——或者用安玛丽·摩尔的术语来说,在照护环境的选择中,存在事实和价值的混合。但是劳拉认为的“有效”和她父母的设想并不是一回事。父母眼中照护的条件——在家中获得自由而非控制,让她远离体制机构——与劳拉想象中的独立在概念上相左,甚至他们对整个康复过程的想象都是不一样的。劳拉渴望拥有“乱来”的能动性(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愿望仍然陷于生活经验的泥沼中,这需要考虑“治疗外”和“治疗中”发生了什么。不幸的是,在成瘾的情况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会得不偿失。
劳拉最终选择了住院治疗而不是去“外面的”私人诊所就诊。但这究竟算是什么样的选择呢?这可以算作自我照护吗?又或者只是在医疗消费主义逻辑下的一种选择?
到头来,我们只剩下选择的逻辑、符合机构和治疗要求的照护的逻辑,对照护的想象以及对照顾的渴望(在药物治疗中、在家庭中、在场所中——仅仅需要身处治疗中心),因为诊所和其他地方都可以提供治疗。最后,我们还剩下复杂的个人行为评估,却避而不谈简单的个体能动性。
原文作者/[美]托德·迈耶斯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