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7幅契丹文帛画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山海经》帛画如何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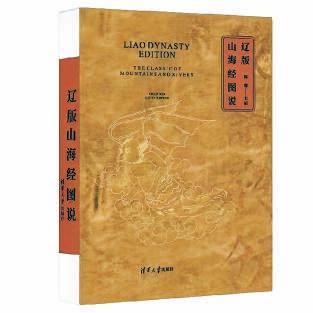
《山海经》是一部以神话故事记录上古历史的奇书,近日,一部新出版的《辽版山海经图说》却受到了一些学者专家的关注。这部《山海经》是由契丹文的347幅丝帛画卷组成,是一部以展现辽代《山海经》帛画为定位的画册。全书以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这8卷为编写架构,展现了300多幅珍贵精美的辽代《山海经》帛画,这些帛画上面有珍贵的辽代契丹文字,整体画风古朴典雅。
辽金文化研究者李肇伦在鉴定过这批辽版山海经后感叹:“当我们触摸这批契丹古帛画时,那极薄柔软的材质令人震撼,与现代织品完全不同,鲜艳的矿物质颜料在显微镜下闪闪发光,犹如宝石般美不胜收。”

◎丝帛《山海经》的抢救
事情还要从陈馨偶然遇到一批罕见的丝帛讲起。原籍北京、久居广东的陈馨不仅对辽金文化热爱至深,十余年来研究不辍。她本人还是长期从事织物贸易积累,对丝织物的认识眼光独到。很多年前,痴迷古物收藏的陈馨在参加一次雅集时,忽然间发现了这些帛画,不过她仔细看发现,画上写的是契丹文,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便觉得有些失望。然而再看一眼,她发现了《山海经》中她最喜爱的“千古第一型男”——刑天,再一找,还有后羿、应龙,以及其他早就烂熟于心的神仙异兽。陈馨感到一阵窒息:这难道是契丹文版本的《山海经》吗?这些帛画是真的还是仿的?
重重疑惑之下,她马上联系了国家博物馆民俗考古学家和鉴定专家宋兆麟先生,见到这几张帛画,宋先生也惊呆了。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些画的出处,画主人说是来自域外的一座古代寺庙。经过反复观察后,宋兆麟说服画主允许它将几幅画带回去仔细研究。几天后,宋兆麟给陈馨打电话,说:“这些帛画非常珍贵,确定无疑是辽版的《山海经》,这可是辽代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赶紧抢救,看看有多少张,能否全部拿下?”就这样,陈馨再次和画主人商讨,募集到一笔费用就买一批,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把帛画彩绘图全买了下来。
绢帛是造纸术发明以前一种极为珍贵的书写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即为例证。这套帛画实际是一部帛书,装裱好的话,应该以卷装的形式呈现出来,显然这是一堆尚未完工的半成品。
2017年,宋兆麟建议陈馨将收藏的这套带有契丹大字的辽版山海经帛画整理出版,因为出版是对这样珍贵的资料的最好的保护和挽救。这套《山海经》图一共347张(每张约60×83厘米),全部是矿物颜料彩绘,左图右书,十分规范。经过整理核对后,能够跟《山海经》经文对上的共340张,这样可以提供给有兴趣、有能力深入研究的同好们。在整理这套帛画时,陈馨跟宋兆麟曾多次深入探讨整理思路,应该关注哪些重点,并在宋兆麟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画中高眉深目的“胡人”何来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陈馨产生了疑问,其中之一便是,这套辽版山海经帛画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眉深目、红毛卷发的胡人。此前学界一致认为《山海经》的古图早已遗失,南朝梁人张僧繇重绘山海经图,传至宋已残阙;宋人舒雅依据张僧繇残本,重绘山海经图十卷,这十卷图本究竟是否传了下来?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就《海外北经》里“深目国”评注时说:“深目类胡,但口绝缩。”大意是深目国的人就是胡人,只是人们绝口不提罢了,说明郭璞时代《山海经》是有经有图的。那么郭璞所赞之图是怎样一个来源,是谁画的呢?
陈馨看来,今日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多是明清版本,其图画部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似乎没人考证过。这套辽版山海经帛画,左图右经,图文并茂,很好地印证了郭璞关于《山海经》有图的陈述。她还注意到,在创作畏兽和山神等核心形象的同时,画家把相关的远山、江海、树木和花草等一并绘制出来,笔触细腻生动,艺术表现力很强,画面感十足,让观画者有一种穿越时空被带入画面的感觉,跟同时期辽国佛教题材的绘画手法和艺术风格一致,应该是那个历史阶段辽国上层社会记录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手段。
契丹人为什么会关注和保存《山海经》?陈馨认为,当年契丹建国后,曾经重用汉人并参照中原汉政权的建制建立官僚体系,引进并模仿中原先进的汉文化,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元人编写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发展而来,当年炎黄涿鹿之战,炎帝战败,其一支后裔迁往辽西,极有可能成为宇文鲜卑的祖先。在《周书》中,有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因此,契丹人把炎帝称为自己的始祖。这似乎为契丹人绘制并保存《辽版山海经》找到了可靠的理由。
◎辽代史料中寻蛛丝马迹
听说有一批辽代绘制的契丹文《山海经》丝帛图时,历史学者孙见坤的内心是颇为诧异的——在他的记忆中,辽代似乎没有人或文献与《山海经》有关;而且在宋代,《山海经》的流传范围相当有限。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就曾说,《山海经》“今独《道藏》有之”。他四处搜求了近二十年才得到一部,令他感叹“《山海经》虽在,亦且亡矣”。而遥远的北方辽国,又怎么会有人想要去绘制一部几乎完整的《山海经》图呢?为此,孙见坤还专门翻阅了陈述先生的《辽史补注》和《全辽文》。在这两部堪称辽代史料集大成的著作中,依然没有找到《山海经》的蛛丝马迹。
直到他拿到《辽版山海经图说》,这一疑问依旧没有消除。通过书前的序言,孙见坤大致了解了这批契丹文《山海经》图发现、整理、出版的过程。宋兆麟先生的鉴定意见无疑能大大减轻读者对这批图的怀疑,但依旧难以解答之前的疑惑:在辽代,会有人读《山海经》,并进而画出这么一大批图吗?
拜近年来古籍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所赐,孙见坤意外地在《宋史》的《刘敞传》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刘敞是北宋时期一位比较重要的学者,他有一次奉命出使辽国。路过顺州时,当地山中有一种怪兽,“如马而食虎豹”,当地契丹人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刘敞听后告诉他们:“这是駮啊。”随即将《山海经》《管子》等书中的有关记载背诵出来,契丹人十分惊叹佩服。鉴于契丹人对于学习中原文化一向十分热衷,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推想,经过这件事,他们很有可能向宋朝求购《山海经》等典籍,并在其境内传播。孙见坤推测,有一位热爱甚至痴迷山海经的人,绘制了一套《山海经》图,并将《山海经》相关的内容翻译成契丹文字——这种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虽然这些只是基于刘敞出使契丹故事的推想,但这至少说明,在辽国阅读、流传山海经,并为其绘图,有一定的可能性。
◎随之而来的争议
《山海经》是先秦时期的文化百科全书,其特点就是有大量插图,俗称“图文书”。过去学术界围绕先有经还是先有图的问题曾争论不休。从文化发生学视角来说,《山海经》是先有民间传说,文明时代以后由文人将其记述为书,画家则绘其图。晋代郭璞、陶渊明曾谈到过《山海经》图。梁代绘画大师张僧繇曾绘过十卷本《山海经》,北宋舒雅也重绘过,然而都失传了。目前学术界所涉及的《山海经》图都出自明清版本,是否有更早的《山海经》图就不得而知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没有真假,只有先后”,认为比鉴定真伪更重要的,是梳理历朝历代不同版本中画面流变。
孙见坤在仔细研究这批布帛后认为,从绘画技法上看,这批契丹文山海经帛画的画面比较粗糙、稚拙,与传世的辽代名画《山弈候约图》等相去甚远,但是,细看其中神灵和人物的画法,依稀与应县木塔所发现的辽代《神农采药图》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这批图的确是辽代遗物的话,那它们很可能也是出自民间画工,而非上层文人、画师之手。其次,这批图采用的是一图一物的模式,基本按照原书顺序排列,这种绘制方式与现存的明清以来的各种《山海经》图基本一致。而与已经失传的张僧繇、舒雅绘本不同,舒雅的绘本是将所有画的内容分类编排,并不依据原书次序,而舒雅本又是依据张僧繇绘本重画的,那么很可能六朝以来的《山海经》图使用的都是分类编排,而非顺序编排。倘若这批帛画的时代确认无误,或许可以将其视作《山海经》图由分类编排到顺序编排的一个过渡。当然,考虑到这批图被发现时已经是散面的状态,其原本的编排形式也可能并非写作所见到的样子。

孙见坤看来,任何新发现的文物或文献,往往都免不了争议,契丹文《山海经》图也是一样。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存疑者、质疑者、否定者肯定会出现,而且人数恐怕还不会很少。但这本书出版的价值之一,或许正在此处。对于任何一份新发现的材料来说,将其完整地公之于众,让大家去讨论,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
(原标题:《山海经》帛画如何现世)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 胡月
流程编辑:U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