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文学的县城文学:当代青年的乡愁寄托,还是一场傲慢拙劣模仿?
转自:上观新闻
局促杂乱的建筑,随意停放的电瓶车,表情忧郁的青年男女,昏黄或青灰的滤镜……
一种被称为“县城文学”的照片和短视频正在社交媒体上流行——尽管被称之为“文学”,其实与文字无关,而是一种视觉风格。
相比单纯追求景色或人物好看,正在流行的“县城文学”强调的是美丽之外的“故事感”——通过那些特意寻找的布景和精心调整过的表情,让观众从图像中就能“脑补”出整个故事。在一些拥趸眼中,这样的影像风格跳脱了对空洞乏味美丽的追求,以影像叙事,是一种新的创造,也是青年人的乡愁。
然而这样“美丽而哀愁”的县城文学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县城文学充满了一二线城市青年对县城生活的刻板印象和居高临下的凝视,“现实生活中的县城并不是这样,互联网不能代表生活的全部。”

小红书上的“县城文学”中,有不少其实是在一二线城市拍摄的。
身着蓝白色运动校服的少女坐在门前,额前发丝纷乱,背景敞开的大门内,是一双模糊的似乎在争吵的身影。画面被调成一种青灰的色调,显得既怀旧又肃杀。再配合上照片标题《“我一定要上高中”》,便成了一张如今流行的县城文学照片——即使只有一张照片或是一段短视频,观众似乎看完了一整个故事。
在小红书上搜索“县城文学”,能找到许多视觉风格十分相似的照片:杂乱而略显陈旧的背景里,面无表情的人物虚影各自行动。美发厅的红蓝白转灯、生锈红漆大门上开出的小窗、褪色的木质窗棂……近景处几件具有明显年代感的物品交代故事背景。画面中心的主人公一般是不笑的,眼神眺望向远方,或坚定或迷惘。再配上昏黄或清灰的滤镜色调,让整张照片更有种“岁月蒙尘”的质地。
县城文学有多火?“重回千禧年之我是县城一姐”昨天登上小红书的热点话题,此前在抖音等平台也多次登上热搜,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甚至将之作为这个月“热点话题”素材,以此教授申论写作。
为什么是县城?
事实上,县城文学早已在不期然间包围住年轻人。4月27日上线的电视剧《微暗之火》,用悬疑故事讲述小镇里的生存百态,而近期备受关注的《我的阿勒泰》则被认为是另一个角度的县城文学。参演了《我的阿勒泰》的演员蒋奇明在去年此时因同样讲述小城故事的《漫长的季节》出圈,其充满张力又与传统“造梦”式偶像截然不同的形象正是如今县城文学的经典,一度被网友称为“招待所男友”。而作品《风流一代》正在戛纳电影节参赛的导演贾樟柯,作品一以贯之地对准“县城”。近年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的摇滚乐队五条人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名字就叫《县城记》。
“如果说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在聚焦中国的乡土情结,那新一代导演更熟悉的是县城叙事。”一些业内人士与部分网友的观点不谋而合:县城具有天然的“文学滤镜”。作为乡村与城市的过渡,县城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和张力;而相比大城市生活高度的秩序化和边界感,县城生活琐碎、平凡、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情绪感受暧昧幽微,既谨小慎微又横冲直撞,充满了奇妙的生命力。
当县城文学从影视、音乐和文学作品逐渐下传至打卡拍照,从专业从业者慢慢渗透到普通人,这一波社交媒体上的县城文学潮流似乎顺理成章。
“比起普通打卡拍照,县城文学最大的魅力是故事感,就像电影剧照,甚至就是电影。”喜欢拍照的杨婷表示,比起春天拍摄樱花或是到景点打卡,县城文学不一定需要人物美丽的,“比如头发可能是乱的,衣服可能也不算漂亮,但是情绪是饱满的。”在拍摄这样的照片时她要摆出的动作表情不再是为了“显腿长”“脸好看”,而是为了“故事感”。“比如照片要表达的是当代中国‘出走的娜拉’,在县城告别男友到北上广谋生的年轻人,那肯定不能只是微笑,而是要有既恋恋不舍又坚决的神情,这对喜欢拍照的人来说很过瘾。”
就像被拍摄者如演员一般“创作”,摄影师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一丝“导演”的吸引力。曾从事职业摄影工作的关磊重新拿起相机拍摄县城文学,“比起原先商业拍摄取景地固定、造型姿态固定,县城文学需要设计故事、寻找场景,还要跟模特、客户讨论造型、姿态和表情,这个过程很过瘾。”
而这样的视觉语言,也让一些异乡漂泊的年轻人寻找到一丝乡愁。抖音上的摄影师“乌鸦JEWEY”被认为是最早拍摄县城文学的人之一。在他发布的不少照片的评论区里,都有网友根据图片撰写“微小说”。摄影师本人也在回复评论时表示自己童年时期是九十年代,青少年时期成长于千禧年,“见证了小城市变化最大的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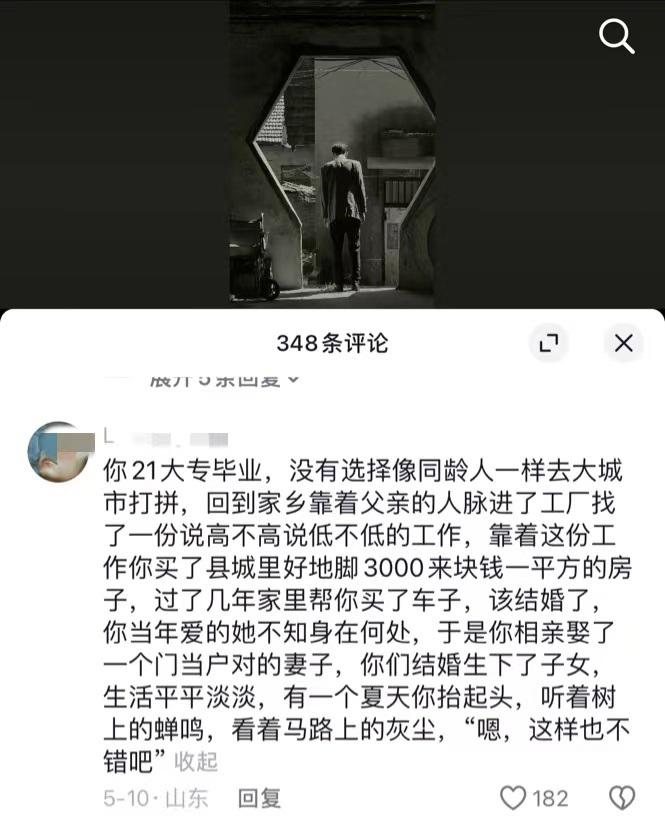
“乌鸦JEWEY”的评论区,常有网友根据照片“脑补”出一篇“微小说”。
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交流如何拍出县城文学,例如上海的川沙老街就被一些网友认为“能拍出县城文学感”——这正是县城文学被诟病的问题:照片与视频中模仿的县城根本不是现实中的县城,“充满了大城市年轻人对县城生活的猎奇、审视和臆想。”来自重庆郊区县城的刘女士以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县城文学照片为例,图中女子身着蓝花立领旗袍和素色布鞋,“二十年前我也从未穿过这样的服装。”她还特意询问了身边来自江苏、浙江等地小城市及县城的朋友,“江南县城的年轻人也不这么穿着啊。社交媒体的县城文学,和之前流行过的任何一种拍照风格和滤镜一样,是一种矫揉造作的顾影自怜,随着新潮流的兴起又快速被淘汰。”
视觉错误在批评者眼中只是最直观的问题。“我那会儿穿的衣服品牌,在我到上海读书时,南京路上也有,星巴克也在开拓县域市场。”大学之后回到家乡工作的岳女士表示,从影像风格到社交媒体话题,如今的“县城议题”变得越来越扁平和刻板,“县城文学里的女孩从来不笑的,都有种挣脱牢笼的感觉。”她发现近年社交媒体上的县城议题,不是“逃回县城”就是“县城逃回北上广”,县城要么被描述成安逸舒适的生活,要么被描述为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利益勾连。“我父母是普通工人,我是自己考上现在的工作。县城的生活也是多元的,也有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它不应该被框定在青春疼痛文学的阴影之下。”
西部某县城的罗先生在国内很多城市生活过,他担心原本文学艺术和社会学领域的县城文学“下沉”至社交媒体后,将原本严肃的议题轻量化、扁平化,反而掩盖了县城这一特定空间真正需要被社会关注的问题。“我老家所在的城市本来以工业为主,近年来在艰难转型,原本在整个城市里比较落后的县城,因为良好的环境和旅游资源吸引了一波投资和大量游客,反而成了最好的区域。”在他看来,“不管是县城文学还是旅游热门的‘网红小城’,社交媒体的巨大流量确实给了千千万万县城被看见的机会。但资源有限、机遇较少、改革缓慢、人才流失这些喧嚣背后的问题,才是热闹背后县城必须面临的问题。”他强调,“互联网不是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