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兴衰:铁血首相与商人,在那个时代各取所需
“铁血首相”俾斯麦、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这是一对曾经在德国政坛叱咤风云的组合,前者在台前呼风唤雨,后者在幕后提供支持,正是这“金与铁”的组合,奠定了德意志帝国的崛起。
但一切总有结束时,弗里茨·斯特恩在《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一书中写道:“俾斯麦时代结束了。布莱希罗德直到最后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最后几周的不确定中,他是活动和阴谋的中心。形形色色的人和派系都试图利用他,但他为俾斯麦所做的努力失败了。他甚至要为此承担些许责任。因为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就像帝国在凡尔赛诞生之时——布莱希罗德的形象让德国精英潜在的反犹主义公开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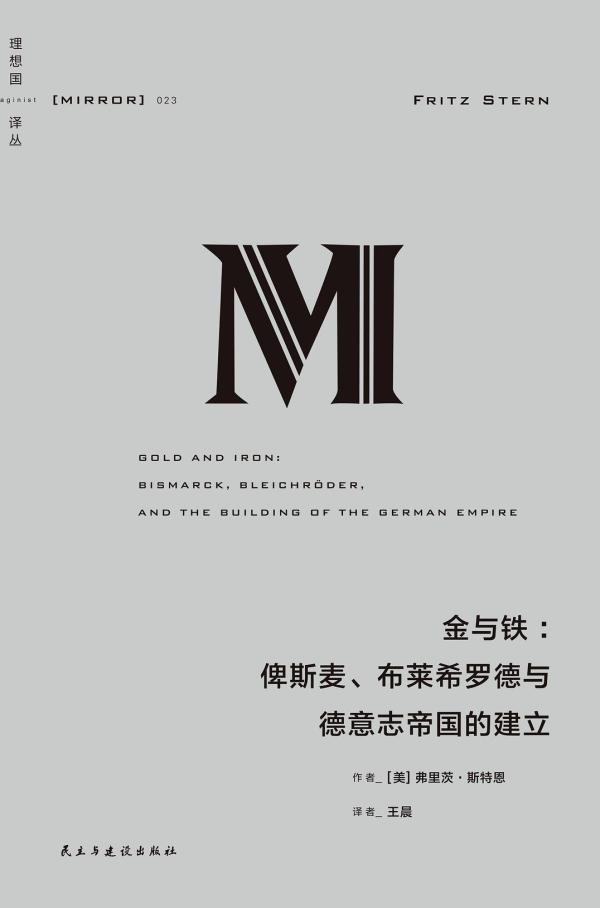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美]弗里茨·斯特恩著,王晨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1月版
此时的布莱希罗德曾流下眼泪,在斯特恩看来,他的眼泪并非政治人物的表演,而是真心的。因为“他与俾斯麦的亲密关系已经维持了二十八年,与那个伟大人物的相处无论有时多么艰难,它都让布莱希罗德在感觉和实质上拥有重要性,那是他身份的一部分……剩下的只有悲伤,因为他与权力的联系被切断,他为大人物服务的习惯被打破。俾斯麦的倒台也意味着布莱希罗德的失势,他特殊的太阳落山了。眼泪是为自己而流。”
保守容克与犹太银行家的各取所需
弗里茨·斯特恩试图在《金与铁》中诠释这样一个事实: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上的演讲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钱与煤铁,而不是铁血。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背后,是德国政界与金融界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新世界和古老封建旧制度的碰撞。
同时,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他们的成功及社会流动带来的利益冲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国及其统治阶层的脆弱,更展现了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希望。
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出身金融家庭,父亲就是银行家,他子承父业,并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也赢来了名字中的“冯”字——这是贵族的象征。但这一切来之不易,当时的犹太人被基督教敌视,始终生活在社会边缘,只能依靠那些非犹太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来谋生(比如放贷和沿街售货等),基督教则因为犹太人的谋生选择而指责他们只关心钱,却未想到他们只能如此。越是拥有财富的犹太人,就越渴望能够融入上流社会。但即使布莱希罗德在1872年被擢升为世袭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观感也没有太大变化。而且,布莱希罗德的成功和努力,并没有让犹太人整体受益,反而还为精英犹太群体招致更多恶意。当时的普鲁士贵族总是有求于布莱希罗德,却又耻于和他公开扯上关系,表面对他客客气气,背后却百般贬低。
奥托·冯·俾斯麦名字中的“冯”并非后天争取而来,而是出生自带,这是容克身份的象征,其家族史甚至比普鲁士王室还要悠久。
一个是在备受压迫的犹太人群体中成功脱颖而出的巨商,一个是容克出身的顽固保守者,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合作在那个时代并不常见,甚至看起来有些违和。但在那个历史当口,他们确实不谋而合,各取所需。
普鲁士容克不同于人们熟悉的英法贵族,他们粗野简朴,不尚奢侈,当然,这更多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即使俾斯麦在容克阶层中已经相当富裕,仍然需要支援。因此,当一个容克希望在政坛有所作为时,一个需要政治力量给自己提供庇护、实现阶层跨越的犹太有钱人,反而会成为他的最佳拍档。
这也跟俾斯麦曾经的年少荒唐有关,他有过花钱如流水的日子,但背上一屁股债后,父亲拒绝为他偿还。经此一役,他显然痛改前非。尽管在政坛闯荡时,有布莱希罗德为之保驾护航,他仍然对经济极其敏感,生活也非常节俭。当然,这种看起来雷厉风行的节俭也更契合“铁血首相”之名,虽然实质上的俾斯麦,是一次次经济发展的重要获利者。
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最困顿的时候来到其身边,也为俾斯麦做了太多事。普丹战争的胜利、普意同盟的促成、克尼格雷茨战役的获胜以及普鲁士随后获得的德意志霸权,是俾斯麦合纵连横的成功,布莱希罗德也都参与其中。他的奔走筹款,让普法战争的胜利天平最终倾向普鲁士,他大大推动了铁路国有化进程,还参与了德国的非洲殖民。当然,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在很大层面上并非正大光明,俾斯麦虽然是普鲁士崛起的重要推手和受益者,但基于自己的出身,更倾向于保守派,因此也很难真正为布莱希罗德这种为自己提供金融服务的“手套”站台,甚至会将对方放在隐秘处。
布莱希罗德也接受了这一点,甚至不惜为此做出许多违心之事。比如说,出于金融专家的直觉,布莱希罗德肯定希望放贷给那些安定繁荣的国家以确保收益,但俾斯麦显然更希望把钱用在那些能够虽然乱,却能给自己带来政绩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布莱希罗德只能放弃自己的常识认知,为俾斯麦服务。这也是德国资产阶级(以犹太人为主)软弱的一面,他们无法像英国同阶层那样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对民主代议制的支持并不坚定,因为自身地位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附于权力,被保守势力轻易拉拢。
普鲁士需要伟大人物扭转国运时,总有人会出现
为俾斯麦服务,也就是为德意志服务。在世界历史上,从小国变身大国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普鲁士的崛起,堪称最传奇之一。
1415年,普鲁士王国的前身——勃兰登堡选侯国,仅仅是神圣罗马帝国所有选侯国中最不起眼的那个。可是到了500年后的“一战”前夕,它已统一了德意志,成为德意志的绝对主导,让德国崛起为争夺世界霸主之位的欧洲强国。
一个国家如何在500年间改变自己?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这个过程也绝非坦途,在普鲁士的崛起过程中,曾有四次衰退,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的危险。尤其是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面对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等组成的联军,普鲁士一度陷入绝望。面对拿破仑时,普鲁士一度被瓜分。但在这些历史的紧要关头,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等横空出世、力挽狂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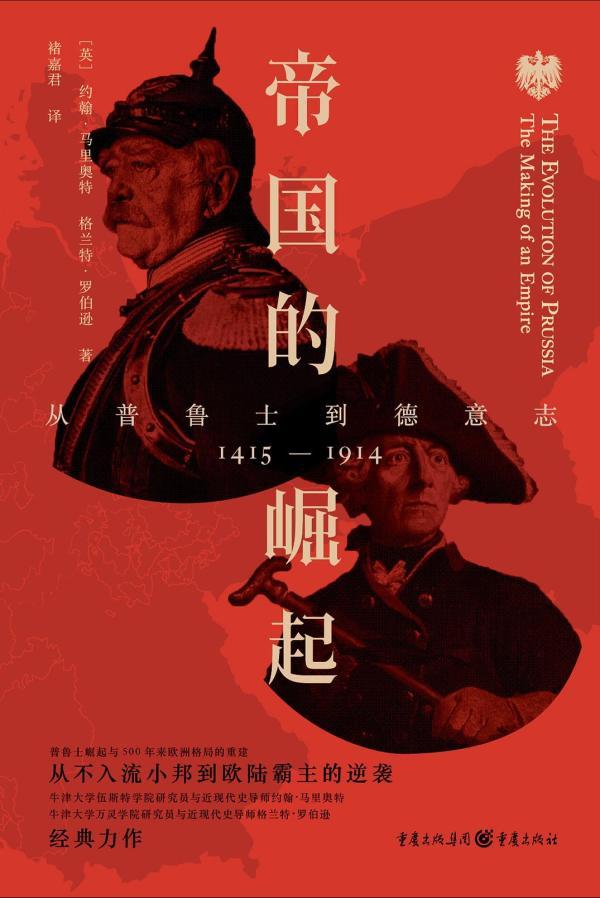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马里奥特与格兰特·罗伯逊在合著的《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中总结道,纵观德意志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普鲁士需要一位能铭记教训并善于探索的伟大人物扭转国运时,这位伟大人物就一定会出现。
腓特烈大帝就是典型例子。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大帝继位,从此开始长达46年的统治,带领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腓特烈大帝被后世誉为最典型的德国人,他意志坚定,永远信奉绝对理性,将国家利益视为一生追求和最大责任。对他而言,普鲁士的强大高于任何其他考虑,甚至让他行无耻之事也在所不惜。在任期间,腓特烈大帝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不择手段,各种暴力和欺诈从未停止。
腓特烈大帝的作风也是德国后来者所坚持的,俾斯麦就是如此。当然,俾斯麦比腓特烈大帝更擅长诡谋,也更能退让和忍辱。他在外交场域表现最为出色,周旋于欧洲各国之间,几乎算计了所有人。当然,也正如书中所说,俾斯麦在“性格和行为中有太多需要批判或自省的地方”,他的本性是“冷酷、执着、粗俗而又追求自我满足的”。《金与铁》中也写道:“俾斯麦作为政客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其见机行事的能力,寻找(有时是营造)正确的时机和突然的机会,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和技巧利用它们。长期规划必然导致选择面缩小。俾斯麦将不愿做选择这典型的人类特点提升为一种至高的政治优点。发明“多重选择战略”最能体现他的天才。”
俾斯麦与大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就展示了他的外交技巧和不择手段的作风。
以1863年为例,当时丹麦国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腓特烈七世去世,因为无嗣,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居民多为德意志人的公国,归属权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俾斯麦决心把这两个公国收入普鲁士囊中,而不是交给所谓的德意志“邦联”。他希望将与此关系不大的奥地利拉进来,成为自己的筹码。但奥地利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除非吃错了药。长袖善舞的俾斯麦却以自己的方式说服了奥地利,有意思的是,他利用的是专制者的恐惧,“奥地利君主做出了愚蠢的判断,以为除了与普鲁士合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抑制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所以抓住了普鲁士伸出的友谊之手,但这只手将给奥地利及其君主带来深深的羞辱。”
结果,普鲁士与奥地利携手出兵,迫使丹麦在次年签订《维也纳和约》,将两个公国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这次掠夺招来全欧洲的指责,因为它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和原则,被视为仅次于瓜分波兰的霸道掠夺。
但俾斯麦显然不在意这样的风评,何况有奥地利一起背锅。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下一步如何一脚踢开奥地利,独占这两个公国。
于是,俾斯麦继续在外交场域展开攻势,一方面与俄罗斯确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著名的比亚里茨会谈,利用后者对法国国内形势和自身权力的焦虑,成功说服对方。但最有趣的是,俾斯麦在比亚里茨会谈中给了无数暗示性的承诺,但一份真正的文件都没有签署过,这样的手腕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年中,俾斯麦一方面利用奥地利,将它拉上进攻丹麦的贼船,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硬的对奥立场,并时刻准备着对奥战争。早在1863年,奥地利提出要所有诸侯国君主和利伯维尔齐聚法兰克福,大家一起商讨德意志邦联的改革以及如何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唯有普鲁士拒绝邀请,这是因为俾斯麦坚持“奥地利的改革方法并不符合普鲁士王室的地位与德意志人民的利益”。
《帝国的崛起》成书于1915年,两位作者当时并不知道一战的最终解决,更不会预见到二战。当然,他们对德国历史的解读并不过时,对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等人的描绘,甚至点出了德国未来步入歧途的“基因”。
《金与铁》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是流亡美国的犹太学者,他于1926年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一户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938年受德国国内形势所迫而移居美国。曾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生活五年的经历,让他始终在探寻一个问题:“邪恶的普遍可能如何在德国成为现实?”
他的答案是,德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是在“瘸腿”状态下进行,政治和经济始终没有同步,权力配置也完全脱节。产业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和掌握土地的贵族并存,偏偏后者依然掌握着政治权力,这也使得德国处于一种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状态,未能转型为正常的民主现代国家,最终走向纳粹主义。
俾斯麦的政治手腕令无数权谋爱好者崇拜,但这恰恰阻碍了德国的转型,使得德国统治阶层没有放弃垄断权力,更没有建立更公平的政治体制。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曾经有过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后就是金融市场的崩溃。俾斯麦抛弃了短暂的自由党盟友,并在1878年大选获胜后推动自己的保守主义道路。
对于犹太人而言,这也并非好事,弗里茨·斯特恩认为,在德国,“贫穷而贪婪的武士—地主阶级的道德支配意味着金钱话题满载虚伪和禁忌,比类似情感以某种沉默形式存在的其他国家更加严重。一门心思关心钱没有好处,但就像德国的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否认钱的重要性,或者向往由荣耀或美德而非金钱决定地位的田园诗般的过去是一种惬意但危险的幻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民族主义出现好斗和排外的特点;比起其他地方的狭隘,它甚至更加无法容忍多元文化,或者既在国内保持团结又与国外维持特殊关系的少数族裔。”
也正因为这样,《金与铁》中这样诠释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它)反映了他所属的两个世界的某些基本过程,其中一个是他诞生的地方,另一个是他迫切渴望的地方。他生来是犹太人,选择成为德国人。多年来,他认为自己可以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与犹太世界的私人和松散的关系不会与在德国世界中的公共和更重要的角色发生矛盾。事实上,他的中年见证德国人与犹太人社会最风平浪静的融合时期,他的晚年则出现对这种融合的第一次有组织否定,他的成功本身被视作否定的理由。”
被遗忘的布莱希罗德
随着威廉一世的去世、愈演愈烈的反犹骚乱,让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这对曾经坚不可摧的同盟最终瓦解。俾斯麦无法解决与威廉二世的矛盾,布莱希罗德则成为牺牲品,俾斯麦也在1890年黯然下台。
可以肯定的是,俾斯麦始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对一切的判断都基于利益。在需要经济支持时,他会借助犹太人的力量,但当反犹主义高涨,同时犹太人中的新兴阶层又支持自由派,与自己的保守理念相抵触时,他又会将布莱希罗德这位亲密战友放在尴尬境地。尤其是1879年,因为最大反对者进步党的领袖多是犹太人,俾斯麦对反犹主义也越发纵容。此后反犹主义成为德国政治斗争的重要基调,在俾斯麦下台后仍然延续。
而且,布莱希罗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消失于历史记录中,也与俾斯麦本人在回忆录中的避而不谈有关。当然,在俾斯麦下台后,布莱希罗德维持着与他的友谊,这显然超脱了功利性。毕竟,在俾斯麦执政后期,亲信纷纷背叛,他已经淡忘了何为忠诚。
弗里茨·斯特恩还写道:“这遗忘与金钱有关,更与德国政治与社会上的迅速变迁有关,与罗斯柴德尔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莱希罗德家族的金钱未能持续太久。犹太人从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希特勒时代,从一个身份焦虑时代进入一个被清除的时代。”
晚年备受反犹主义困扰的布莱希罗德,在1893年去世时反而极尽哀荣,这是因为他晚年在慈善事业上的努力,因此德国新闻界称他为“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
《金与铁》中写道:“布莱希罗德没有墓志铭。他留下一个成就、胜利和毁灭的故事,一个徒劳的希望被历史潮流撕碎的故事。他是德国社会大转变的一部分;他的人生(包括成功和痛苦)折射出那个社会的活力和有缺陷的特点。他的多重公共角色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但甚至他的私人生活也被他与一个迷人但不友好的社会的茫然斗争所支配。他同时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和奴隶。德国最富有的人远非最自由的人。他的故事讲述他本人和他人对他的狂妄,讲述黄金锁链如何蒙蔽人们的双眼,让他们接受钢铁般无情的奴役。他人生中的某些教训远比他的影响或财富更加重要:它们是他永恒的纪念碑。”
而在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身后,德国一步步走向灾难。继任的当权者比俾斯麦更加贪婪,却又没有后者的精明谨慎,从一战到二战,背后是德国政治的缺陷与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