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家中的天使 创造自己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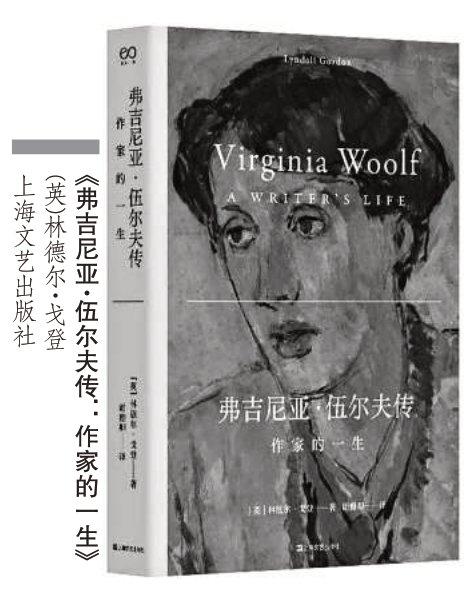
▌林颐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这个书名平淡到难以吸引读者的视线,假如它的传主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而作者不是著名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的话。
林德尔具有出色的传记写作能力,她能够敏锐地体察写作对象的心思,捕捉作家生涯中隐藏的轨迹。原来,她也是受到了伍尔夫的很大影响。这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并非只是对某位作家的生平梳理和文学研究,它也是伍尔夫设想中的“新传记”写作的一个杰出样本。它是一项致敬,对于那些别出心裁的、喜欢探索的、有足够智慧和勇气、能够开创某种风气的人们的致敬;它是一种文学对话,体现了传记写作的最大意义所在,写作者也是被写作者,再现作家写作生涯的过程,呈现的是生命能动性的诠释方式。
林德尔通过伍尔夫的小说作品以及日记和书信重构了伍尔夫的生平。伍尔夫写有六卷书信、三十八年的日记(出版有五卷本的日记选,第六卷收录了她早年的日志),还有六卷散文,而且她的小说也包括了大量的自传性元素。写伍尔夫传记所需要的,就是在纷繁的材料中,准确地抓住那条最明晰的、最能体现作家个性的线索。
林德尔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她意识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之于传记文学创作的特别意义。传记的核心,是人物。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伟人们取得的成就,但很少有人去分析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对于行动的影响,更疏于对普通人的观察。伍尔夫在其所处的时代,用新锐的观念和实践,改变了长期沿袭的、固守成规的做法,而这也影响了伍尔夫自己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理念,促使其成为“现代性”的开创者。20世纪的文学、历史、哲学等众多领域都开始用新的视角去审视普通人的活动,去注意微观的流动之于宏观的社会发展的意义。
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批评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保守派文人之一,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却成为最反叛的、最先锋的,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现代派先驱作家之一,研讨这种继承与革新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在弗吉尼亚很小的时候,她就被认定会成为一个作家,她是斯蒂芬家孩子里最有文学天赋的。这当然与父母寄予的厚望,特别是父亲对她的激励大有关联。在一封家书中,莱斯利写道:“即便我能,我也不愿你违背自己的判断行事。”林德尔说,斯蒂芬对待女性不落俗套的方式给了女儿一张重要的许可证,但与此同时,这也使他的认知盲区格外地让人恼火。
弗吉尼亚不惮于向父亲发起攻击。她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文写道,一本好的传记“记录的不仅是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包括改变传主人生的事件”。这篇评论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她父亲主编的《英国名人传记辞典》的刻板结构而言的。伍尔夫的文学目标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从维多利亚时代到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那种道德说教的风格。
母亲茱莉亚与大姐斯黛拉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在“纠缠”弗吉尼亚。在1897年的日记和1940年的《往事札记》里,弗吉尼亚强调了死亡不体面的一面,它带来痛苦、暴躁、情绪失控。弗吉尼亚濒于崩溃,思绪混乱,但是,这段生命中的黑暗岁月也使她发现了“觉醒的意识”中那些非凡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幽灵般的知音交流,后来,我们可以在《远航》《到灯塔去》等作品里发现那些曾经被阴霾遮盖的光亮,疯癫与创造力的界限从来难以划分。
林德尔写道,伍尔夫曾经告诉一位朋友,在“疯狂的火山岩”中,她找到了作品的主题:“它喷涌而出,一切都是成型的,是最终状态,而不像在理智状态中是一滴一滴的。”可以在这句话中窥见意识流小说的雏形,这种火山喷发的物质不断被受过训练的智力冷却和塑造,然后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林德尔这部传记的很大特点,也在于她对伍尔夫作品所隐藏的自传成分的挖掘,林德尔对于伍尔夫的重要作品做了显微镜式的切片剖析,弗吉尼亚·伍尔夫构筑了一个特别的文学世界,而她所创作的作品也为这位我行我素的女作家勾勒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轮廓。
伍尔夫把人的自我视作创作虚构作品的素材,伍尔夫的小说人物经常无法确认对自我的感知,内心世界与呈现给外界的人格相矛盾。在《远航》里,雷切尔从船上凝视海底的幽暗之处,感到自己“就像海底的一条鱼”;在《夜与日》里,凯瑟琳被“生而为人永恒的孤独感”包围着;在《达洛维夫人》里,她探索了四年的人性摧残会给一个士兵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奥兰多》里,她刻画了一位雌雄同体的贵族,他(她)的故事贯穿了英国五百年的历史……
弗吉尼亚终身都在探索人的自我呈现及其在历史中的呈现。她对传记文学持有特殊的兴趣,她很清楚传记这一“不纯粹的艺术”所涉及的思想问题,因为人的思想就是那么复杂的,总是被深藏在表层行为之下的。作为传记家的女儿,她挑战着传记的常规,想把传记式的认知转化为创造性的结论。“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我,我也会创造一个你”——这就是《奥兰多》的主旨,或者,就像林德尔所说的,“这是对一个隐秘自我的敏锐透视,也成为她的日记和小说之间最主要的方法论联系。”
在这个过程里,伍尔夫发现了社会期望对于女性人生的塑造。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女性是“家中的天使”,伍尔夫说:“如果我不杀死她,她就会杀了我——作为作家的我。”伍尔夫用《一间自己的房间》等作品表达自己的观点,用它们来反抗被引导的无能和无知——它们如此长久地遮蔽了女性的“反历史”。在伍尔夫的晚期岁月,她尝试去挖掘战争带来的“群体情感”,她发现,“我的梦想太集中于自己了”,于是,她决心“保持匿名”,不再沉浸于自我,而是寻求公众声音的回应,于是,传记成为她重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的方式。伍尔夫认为,传记作家“可以告诉我们的远比又一个事实更多。他可以告诉我们创造性的事实,血肉丰满的事实,能带来启发,正在成形的事实”。显然,在伍尔夫看来,传记具有不可估量的包容性,远比所有的“事实”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
伍尔夫对于传记的看法,以及林德尔这部描写伍尔夫的传记,都在创造性地回应“传记”这种主旨在于呈现人物形象的文学体裁,它在形式、内容和思想性方面带来的挑战。如今,公众心目中的好的传记,基本都要求其就事实与伪饰、信息与阐释、作品的自传性和作者多重人格的隐藏等问题做出解答,这正是伍尔夫所期待的,也是林德尔所体现的。我们应当注意传记作品潜在的丰富性,它开拓了文学塑造的多种可能,并向读者们传递文学创作的不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