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晔读《诗人高启》丨风物重新六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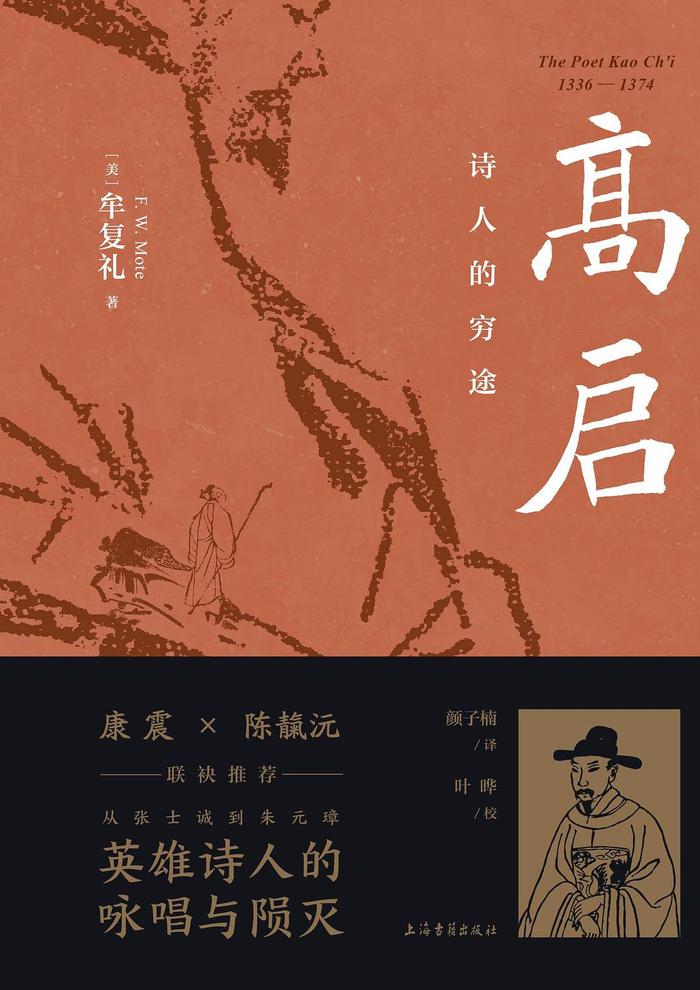
1962年,一位名叫FrederickMote的青年学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诗人高启》(ThePoetKaoCh’i,1336–1374)。尽管这部书在当时得到了刘若愚(JamesJ.Y.Liu)、杨联陞(Lien-shengYang)、韩南(PatrickHanan)、侯思孟(DonaldHolzman)、李铸晋(Chu-tsingLi)等人的专业书评,但朴实无华的书名没能引来更多普通读者的关注。倘若没有日后誉满全球的汉名“牟复礼”加持,即使将这本书放在当今星罗棋布的图书市场中,可能同样会流于平平。当然,历史的事实是,这位年轻人后以《中国思想之渊源》《剑桥中国明代史》《帝制中国:900–1800》等著作闻名中西学界,很少有人记得他曾对一位天不假年的明代诗人早垂青眼。202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中译本,易名《高启:诗人的穷途》(以下简称《诗人高启》),似将预期的读者群体拟定为了文学爱好者。这看似一次学科分属上的错位,但身为历史学家的牟复礼(1922–2005)曾在西方汉学界提倡“文史不分家”(LiteratureandHistorydonotdividetheirpatrimony),如果他看到这部书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中打开生面,想来也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六十年过去了,从传记研究的辉煌到精英史研究的没落,曾经风盛的学术意义早已时移势易。罔顾当代读者之所需、一味纪念逝去的崇高,固然失之老派;但开掘在过去被遮蔽的学术潜能、重焕在今日所合宜的时代光彩,则未必不可为之。在牟复礼的眼中,诗人高启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三十八岁,而当这部专著面世时,四十岁的他至少在人生阅历上已能理解那些常见于青年时代的“英雄主义”心境了。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寄题福帅张子仪尚书禊游堂》一诗中,感慨“祖孙接武禊堂前,风物重新六十年”。作为《诗人高启》的译者,颜子楠教授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生导师卢庆滨(AndrewLo)先生,从本科至博士一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高友工(Yu-KungKao)、浦安迪(AndrewPlaks)教授的高足。由此,将这部书的翻译视为普林斯顿汉学传统下的一次“祖孙接武”,亦无不可。也正因这一层学缘关系,颜教授可以“不要外人来作记,当家自有笔如椽”,为我们撰写了一篇精彩又不失活泼的译后记;而我作为一名关系微妙的特殊“读者”,领略这“风物重新六十年”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像杨万里那样写一篇文章来为之“寄题”了。
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的创立者,一部因传主的诗人身份而未能在历史学界获得足够礼遇的处女作,在迟迟六十年后,终有机会与中国读者重新邂逅。六十年的时间,对一部汉学专著来说,实在是对其学术活力的巨大考验,尤其考虑到当代的中国读者,对这位“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毛泽东书高启《梅花》,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228页)虽没有那么熟悉,但也绝谈不上陌生。它是否依然值得翻译,其中风物又当如何“重新”,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牟复礼著述自身的生命力。而在研究方法迭兴相继的学界风气下,如何在故籍与旧事中获取新知,也是我们在经典译读的过程中尤须思考的问题。
一重“新”:汉语读者眼中的诗人高启
在1950至1960年代,北美地区的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写作曾出现过一波浪潮,这一写作模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之一。以林语堂(1895–1976)《苏东坡传》(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1947)、洪业(WilliamHung,1893–1980)《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Fu:China’sGreatestPoet,1952)、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袁枚:18世纪的中国诗人》(YuanMei:EighteenthCenturyChinesePoet,1956)、牟复礼《诗人高启》(ThePoetKaoCh’i,1336–1374,1962)、刘子健(JamesT.Liu,1919–1993)《欧阳修:11世纪的新儒家》(Ou-YangHsiu:AnEleventh-CenturyNeo-Confucianist,1967)等为代表的一批英文专著,采用了传记写作的方式,将中国的伟大作家推介给西方读者。仰赖于传记写作的叙事特点,这些专著在问世数十年后依然葆有鲜活的生命力,通过翻译回归汉语世界后仍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早在19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就先后出版了宋碧云、张振玉翻译的《苏东坡传》的两种中译本(远景出版社,1977;德华出版社,1979);进入本世纪后,相关译介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如曾祥波译《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刘云军译《欧阳修》(重庆出版社,2022)、颜子楠译《高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等,都是非常出色的译本。
在这些传记作家中,牟复礼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并非林语堂、洪业、刘子健那样的华人学者,也不是阿瑟·韦利那样从未到过中国的老一辈翻译名家。相比之下,他的身上有着浓郁的西方历史学家的气质,更懂得怎样切入西方学界的核心话语,也更懂得如何向西方读者提供适合他们阅读趣味和知识体系的汉学书籍。其中很典型的做法,就是在《诗人高启》中专门设置了“英雄诗人”与“英雄幻灭”两章,用来讨论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二十七年(1367)间青年高启的理想破灭。在英文原书中,牟复礼用了五十六页的篇幅,重建了高启及其社交圈的活动,特别是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北郭十友”。这是一群自信满满的“英雄诗人”,却在张士诚政权覆灭后的复杂感情中,迎来了未知却又注定悲剧的人生新幕。从学术的立场来说,作者对“北郭十友”的考证和对《威爱论》的阐释,即使放在数十年后,亦处在学界的前沿;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引入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的“诗人英雄”概念(见《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10年。以下简称《论英雄》),是牟复礼引导母语世界的读者走近高启人生的重要一环。
与卡莱尔笔下的“诗人英雄”但丁和莎士比亚一样,牟复礼笔下的高启充满了人生命运的张力,甚至更大的悲剧感。《诗人高启》共分十章,以“序幕”“苏州的年轻诗人”“青丘子”“英雄诗人”“英雄幻灭”“南京,洪武二年至三年”“自在的诗人”“流槎”“灾难”“落幕”为章目,如同一场人生的舞台剧,细描了诗人高启在末世动乱中有志难酬、又在王朝新生的政治风云中被无情裹挟并最终遇害的一生。全书没有一次提到但丁或莎士比亚,但考虑到“诗人英雄”的概念在西方中产阶层读者中近乎一种常识,那么,他们作为一种“隐性的在场”其实无处不在,这或许是缺少西方文化底色的中国读者较难感触到的一面。而对西方读者而言,高启人生的跌宕起伏,不难使人联想到但丁“以毕生精力向这个世界作不屈不挠斗争的神态”(《论英雄》,102页),以及他最后通过诗歌来实践其“洞察神圣奥秘”(《论英雄》,95–96页)的伟大事业。这种高效而便捷的暗示,能够让西方读者迅速地捕捉到眼前这位陌生的东方诗人的“英雄”气质:真诚执着,怀有强烈的激情,很难轻易改变其初衷等(《论英雄》,104页)。而作者只需要在引言中预告,高启身上所流露出的中国独有的“英雄主义”(heroism)观念,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英雄主义的“儒家英雄式的美德”(Confucianheroicvirtue),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并且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价值具象化。牟复礼提醒西方读者,如果想要认识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需要理解以下四个概念:一个良好的社会(thegoodsociety),个人将其现实化的责任(theindividual’sresponsibilitytoworkforitsrealization),诗歌的表达功能(英雄个人在面对这些价值观时如何进行表达,theroleofpoetryinexpressingtheheroicindividual’ssensitivenesstothesevalues),诗歌的现实功能(英雄个人如何将这些价值观念付诸实践,theroleofpoetryinevidencinghiscapacitiesfortheirrealization)。不难看出,这是对儒家诗学传统中“诗言志”说的一种西方释义。与之相比,中译本里虽有译者注对“诗人英雄”的一再说明,仍难以弥补中国读者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先天不足,这的确是翻译作品很难两全的一面。
较之上世纪中叶的西方读者,基本上同时读到了苏轼、袁枚、高启等人的第一部英文传记,在当代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中,高启与其他几人相比,仍有不小的声誉差距。因为牟复礼的推重,高启至今仍是“西方最知名的中国明代诗人”(thebest-knownMingpoetintheWest,齐皎瀚语,见JonathanChavestransl.andeds.,TheColumbiaBookofLaterChinesePoetry:Yüan,Ming,andCh’ingDynasties(1279–1911),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122),但在“五四”以来的中国读者眼中,处在晚明思想解放之下的徐渭、袁宏道、张岱等人,显然声名更盛。尽管清代最重要的几部明诗选本都对高启有着很高的评价,甚至如果没有清人金檀的《高青丘诗集注》,牟复礼的研究很可能举步维艰,但在民国最盛行的几部通代文学史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其自序中详列了中、下卷的写作计划)与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1932)强调文学的白话、通俗属性,高启因其传统诗文创作而无缘得列;在断代文学史著述里,钱基博的《明代文学》(1933)与宋佩韦的《明文学史》(1934)对高启的诗歌成就予以了较充分的表彰,但这两部书在整个民国学术版图中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新中国以来,在1960年代通行的北大中文系55级编著(1958)和游国恩等主编(1963)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中,高启都未能成为单独的一节。也就是说,至少在《诗人高启》问世时,一般中国读者对高启的认识,并不比西方读者深入多少。
即使到了2020年代,仍有相当数量的汉语读者既无法准确说出高启的文学史位置,也很难完整地背诵出他的某首诗歌。我们需要摆脱某种观念上的固执并坦然承认,在中、西各自的大众阅读中,狭义的学术史进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心理才是一般读者理解高启之锁钥。我们不禁要问,对于第一次接触《诗人高启》的汉语读者而言,更重要的是体察西方学者(及其预期读者)的“异域之眼”,还是感受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与古人共情”?这就涉及到翻译策略的问题,比如对“英雄主义”等概念的表述、对西式长句及其语法逻辑关系的调整等。颜子楠教授在译后记中也表达了对“汉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不同看法,而他本人是一位颇为原教旨主义的“汉学翻译”者,直言“文学翻译”与屡遭非议的“伪译”(pseudo-translation)只有一墙之隔。这也是我作为校译者需要与他不断磨合的重要一面,即如何在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之间达成一种良性平衡。而在高启这个案例中,是否通过语言的“诗性”来强化诗人自身的“诗性”,就显得颇为关键。
如果我们读卡莱尔的书就会发现,古典式的抒论在其中比比皆是。这固然是十九世纪学者的“通病”,有些“落伍”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理念。但既然牟复礼选择了卡莱尔的“诗人英雄”概念,那么,如何调动汉语读者的情绪、将其引入“英雄”的世界之中,就是中译本需要考虑的问题。着意提醒读者去对卡莱尔的著述作延展阅读,从而更好地领会牟复礼的用心,明显有悖于当下大众阅读的特点,那么,适当地引入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汉语表达方式,在“文学翻译”的环节隐性地感召出读者的“英雄”情结,或可成为另一种策略。眼前的这部《诗人高启》,就是两种翻译思路磨合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结果,可能未必尽如人心,但我们的初衷未变,希望这本书能收获更多的汉语读者,让高启回归他的东方故土,回到他深爱的“吾吴”,进入到数百年后生长于兹的当代同胞的阅读视野之中。
二重“新”:二十一世纪读者眼中的诗人高启
在西方图书界,人物传记一直是类型写作的大宗。《诗人高启》中译本的问世,让这本书的预期读者,从1960年代切换至2020年代,然而,这六十年间阅读理念的变革,无疑超出了原作者的“预期”。从书肆流通到网上阅读,互联网文化下的阅读革命使人物传记的叙事能力、知识基础、价值观念等发生丕变,读者的阅读口味愈发难以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译本需要经受的考验不仅在于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下的阅读习惯转换,同样还有信息时代所养成的各种新的阅读方式。而当今读者所习惯的叙事节奏和信息密度,则是六十年前的写作者所无法想象的。

中译本易名为“诗人的穷途”,固然有基于读者市场的考虑,但在牟复礼的笔下,高启成年后的文学生涯确实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在人生的“途”中。无论是至正十八年(1358)欲有所为的吴越之游(见第三章),还是洪武二年(1369)的应召赴京以及次年的失望返乡(见第六章),每一次出行所携带的理想愿景,皆被无情的现实击碎。我们看到一位“诗人英雄”在一次又一次的离乡与归乡中被逼入人生的穷途。当洪武六年(1373)从苏州南郊搬入城中时,尚未不惑的高启已不复壮游的心态,而是转向了内心的平静。他在《槎轩记》(高启自号“槎轩”)中发出人生命运如“天地间一槎”的感悟,实在是一种痛彻心扉后的淡泊从容。
在英文原书中,第八章的标题为“Driftwood”,中译作“流槎”。《槎轩记》通篇未及“流”字,开篇曰“槎,浮木也”,而浮木可以有各种样态,“或垫或浮,或泛或止”。高启自拟为“漂然而行,泊然而滞,随所遭水之势”的飘泊状态,这与“天河通海”的“浮槎”古典事义相比,已有了较大的变动。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无根之路,诗人自己未必视为“穷”途,甚至是他颇为自得的一种状态,但在我们这些历史旁观者(包括牟复礼)的眼中,高启的前后两截人生呈现出了强烈的悲剧感。对1960年代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基于自身“漂然而行,泊然而滞”的生命思考,不难使人联想到西方文学中的漂流传统。那些作品大多以生存困境为主题,探讨人性、文明与自然等多重关系,展现人物面对孤独、恐惧、绝望等负面情绪时的顽强生命力和求生意志,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这个起源于十八世纪、发展于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与卡莱尔的“英雄”学说一样,归属在二十世纪初出生的牟复礼的一般知识范围内,使他足以信手拈来。高启没有像鲁滨逊那样在真实的海洋上漂流,但战争离乱和政治困苦对他的心理创伤,是另一种形式的“灾难”所造成的“漂流”。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在高启的身上,牟复礼或许看到了恩师王崇武的影子,那种对经历乱世、壮志难酬的不平,对王朝新立、万象更新的期待,以及对中年离世、其道崩殂的遗憾等。当今中国的普通读者,或许终其一生也难与战火和政治纷乱联系在一起,但在变动不居的快节奏社会中,心灵的无根和流荡以另一种方式普遍存在,我们仍可以在高启身上看到足以激起内心波澜的共鸣。如果高启的“流槎”之感与释然心态,可以引发读者对当下社会生存状态的更多思考,那么,我想无论高启本人还是牟复礼先生,都应该会感到慰藉。正如颜子楠在译后记中的自问自答:“身处现代的中国读者从同样的文献材料中又会读到什么?”“传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理解其人其世,更是在于反思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在混乱变动的世界中那些恒定不变的无能与无奈。”
牟复礼自己对《诗人高启》的学术价值,无疑是自信的。他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提到:“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在用中文写作的学者中,自从王崇武和吴晗去世后,对明朝建国时期的研究没有明显的新建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上卷,836页)言下之意,较之汉语学界的苍白,《诗人高启》是这一时期(1950–1975)海外明初史研究的重要硕果。直到二十一世纪,牟复礼对高启的历史评价,依然深植在海外汉学的底层逻辑之中。如孙康宜(Kang-iSunChang)、宇文所安(Stephen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其上下分卷的时间节点选择在洪武八年(1375),就是因为“像杨维桢(1296–1370)、倪瓒(1301–1374)和刘基(1311–1375)等出生在元朝的著名文人均已相继去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朱元璋处决了大诗人高启(1336–1374),开启了文禁森严、残酷诛杀的洪武年代,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下卷,13页)。作为洪武文祸的标志性事件,高启的陨落成为中国文学史“二分”的重要理据,这又是怎样一种悲剧性的“荣耀”呢?
其实,观诸文学史的内部,高启的穷途不只是他个体生命的穷途,也不止于一位理想主义的“诗人英雄”面对时代风云的穷途,还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段穷途。诗人所代表的不只是“英雄”的身份,还有诗歌本身作为一种思想表达方式的存在意义,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牟复礼未予思考的一面。但他在海外汉学界的巨大影响,又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后来者对于高启的文学认知。返观中国古代的评论资源,过去四百年的明诗批评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高启为代表的明初诗人身携古典诗歌的余晖,与十六世纪“诗界革命”未果的复古派诗人相角逐的一段历程。高启在这场漫长的竞赛中处于优势的位置,本质上意味着古典诗歌在明初已走入了穷途,这也是不同时代的批评家所达成的共识性论断。如果中译本书名中的“穷途”二字,能发作者所未发,部分地体现了其身后的或与其平行的学术史进程,为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提供一个甚至多个充满变数的阅读方向,那么我想,即便它多少有违作者的本意,牟复礼先生大抵也是乐见其成的。
三重“新”:本土学界视域中的诗人高启
在二十世纪前中期拿到博士学位的海外汉学家中,很多人通过外交或文化交流的渠道有过来华的经历,但像牟复礼这样在中国大学拿到学位的其实并不多见。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等借外事交流多次来华的西方学人,大多志在现代中国研究,对中国的本土学术传统关注甚少;有良好的本土学术造诣而后在西方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又因其少数族裔的身份,在对传统方法的坚持上略显窘迫,从容者少。牟复礼认为刘子健是“试图将全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工具结合起来的人物”(朱鸿林《追思牟复礼先生》,《〈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456页),为此极力推动他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既归因于牟氏敏锐的识人眼光,也与刘先生是少数几位在中西方法合璧上取得成功的学人有关。
牟复礼先生的早岁经历,可见其弟子朱鸿林教授的《追思牟复礼先生》一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曾服役于美国陆军空战部队,投入中缅印战区行动;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48年获学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有过短暂的深造经历,修读了郑天挺开设的明清史研究课程等;1950年返回美国,1954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至台湾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56年起,历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8年后任东亚学系教授),于1987年荣休。因为有过完整的在华求学经历,他对中国本土的学术体系及动态有较充分的了解。仅就《诗人高启》的中文学术资源来说,王崇武整理的《明本纪校注》(商务印书馆,1948)和同年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十二期上的《读高青邱〈威爱论〉》,以及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49),对牟复礼将早期的治学重心置于明初开国史尤为重要。在专著的扉页上,牟复礼写下“追忆王崇武——恩师·学者·挚友”,这是对王崇武在五年前病逝于北京的沉重追悼。
王崇武先生(1911–1957)是著名的明史专家,牟复礼在南京读书期间曾受业其门下。1946-1948年间,王崇武任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正值三十五岁学术黄金期,其《读高青邱〈威爱论〉》中“以诗证史”的思维路径、对“吴中旧事”的钩沉索隐、以及重视建国问题的政治史立场等,深刻地影响了《诗人高启》第三、第四章的写作。牟复礼在《诗人高启》中提倡“文史不分家”,亦得益于年轻时接受过规范的中国古典学术训练。遗憾的是,这一倡导在1960年代的西方历史学界颇显“异端”,未得到太多的呼应,这从当时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西洋史专家史东(LaurenceStone)称牟复礼为“expertinChineseliterature”,即可见一斑(见陆扬《花前又见燕归迟——追忆牟复礼先生》,《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不过,日后西方历史学界的文化史转向,又多少印证了牟复礼的“先见之明”。
中译本的出版,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这段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历史记忆,它提醒我们反思,怎样的学问才是真正的“走出去”?本土学问又当如何真正地融入世界性学问?牟复礼的学术经历及其身上所具备的某些原生品质,在那个命运多舛、东西冷战的年代,或许不可复制;但在现今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有很多道路可以通往想象中的罗马,如何选择真“正”之路,避免在形式主义的得意中错过了融入世界性学问的机会,同样值得深省。
以中译本出版为契机,《诗人高启》如何融入本土的高启研究,并进入更广阔的明初历史及文学研究之中,亦费思量。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无论是中国明史学界,还是明代文学研究界,对这部书的关注都近乎“失声”。不同研究领域或许各有各的考虑,追责过去亦无必要,但适当地展望未来,却是一种当下的应然。从细微处着眼,在人物实证方面,借贾继用《吴中四杰年谱》等研究成果去纠正牟复礼书中的一些疏误,并非难事,中译本所添加的“译者注”中,不乏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的事实性澄清;在诗歌分析方面,过去二十年以左东岭、李圣华、余来明等人为代表的研究力量,对高启的形象、心态及其文学思想与风格给予了更立体、更细节的勾勒,亦可与书中的文本分析两相参读。从宏大处考量,《诗人高启》长期处在学术“失声”的状态,反而是其作为“学科盲区”的宝贵之处:明清史学界对集部文献的考察缺失,明代文学学界在历史研究法上的捉襟见肘和研究视野上的相对局限,直至今日所得到的改善还是远落后于整体学术发展的进度。人物传记的写法置于二十一世纪或已不再新奇,但正所谓“得意忘筌”,如果能通过某种写作方式,将旧的学科缝隙放大为新的学科空间,那么,又何必在意所用工具的新与旧呢?
在现今学界,近五到十年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被趋之若鹜,儒莲奖、列文森奖等获奖作品,经常在第一时间被国内的出版公司买下版权。这固然是中国学术发展及社会读者需求日益壮大的一种反映,但面对更早的海外汉学经典著作,学界似乎缺少足够的译介动力,大概是觉得无论之于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这些旧籍都已不再是必读的书目。出版商的舍此就彼,自是经过了前期的商业调查,反映的是多数读者的阅读期望,一代有一代的阅读文化,此无可厚非;但作为理性的研究者,挖掘并赋予早期学术书籍更具时代性的内涵,也值得耐心为之。《诗人高启》中译本的更大意义,与其说是向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读者展示一位鲜活的“诗人英雄”,毋宁说提醒我们如何在更多早已凝为经典的海外汉学甚至世界文化资源中,打捞其“重新”的学术能量。
同样是学术翻译,面对西方本土内生的人文资源,中国学界较少去翻译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消化更早期的遗产,以至于某些学人生出了中国的人文社科落后世界数十年的感慨;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大概是对研究对象持有一种更自信的态度,我们倾向于与最新的动态展开直接的对话。站在学术前沿的立场上,这种选择没有问题,但若由此丢失了对早期汉学经典的关注,却难免令人遗憾。对西方读者来说,高启或许只是一位陌生的文学过客,是阅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一抹身影,很少有人会重拾一本六十年前的旧书;但对中国学界来说,《诗人高启》是我们了解西方读者如何认识中国诗人的一个窗口,也是从中国诗人身上感受共有的人类文明特性的一个窗口,旧书所附载的文化属性远远重要于其时间属性。当学术界重新回顾和梳理海外汉学史的时候,对“风物重新”的思考,或许会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及其世界语境引入一面新的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