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读《狼性时代》丨人狼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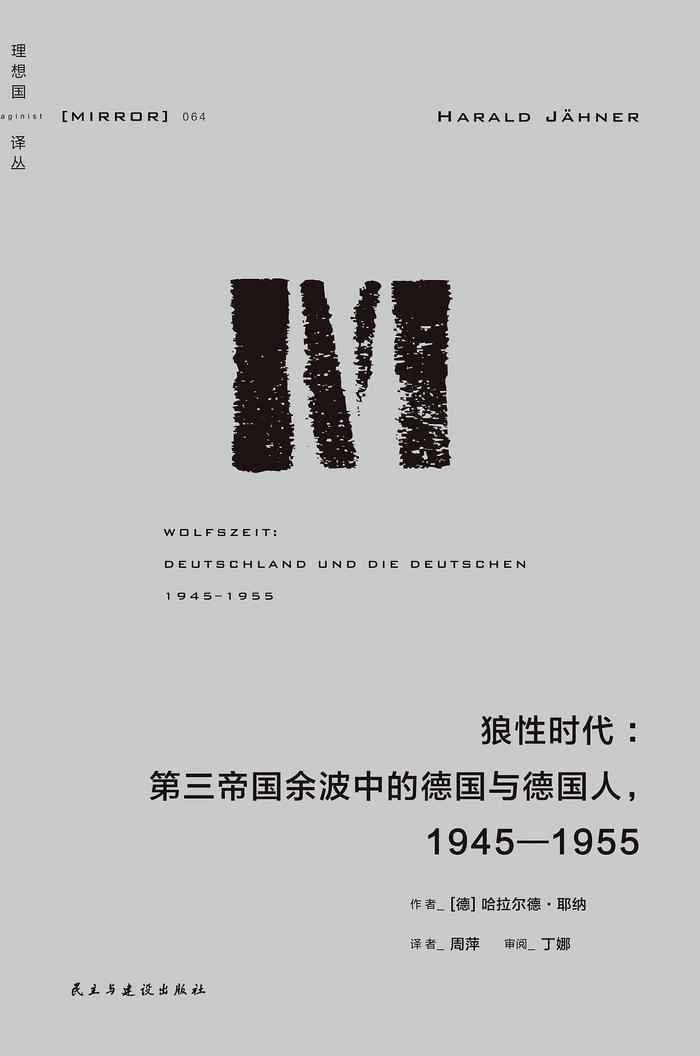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德]哈拉尔德·耶纳著,周萍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32页,102.00元
1944年10月,面对长驱直入攻入德境的盟军,“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宣布了一项全民游击战的“狼人行动”。战争结束前两月,陷入疯狂的戈培尔把这个行动上升为每个第三帝国公民的责任:“在德国土地上的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格杀勿论的猎物……身为一个狼人,拥有生杀予夺之权!”
然而,无论是打穿莱茵河进占德国西北的西线盟军,还是越过奥德河-尼斯河攻下柏林的苏联红军来说,这残忍酷烈的“狼人行动”似乎只是败亡纳粹的疯魔呓语。在艰苦卓绝的战斗结束之后,无论在德国哪里,每当盟军占领一片土地,那里就一下子归于平静。路边站着的不是意图袭击的狼人野兽,而是挥手致意的友善人群,他们从占领者手中接过巧克力并感激涕零。似乎德国人灵魂里的法西斯主义在战败的那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还在,狼在哪里?
哈拉尔德·耶纳给出了答案。这位资深媒体人、文化批评家、文学博士,用自己多年在德国文艺界与社会传媒摸爬滚打的毒辣眼光,揭穿了战后德国人在战败者温驯外表下掩藏的狼性。1945年夏,在德国尚存领土上的约七千五百万人难以构成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在战争废墟、供给困难、占领者间的矛盾与不彻底的去纳粹化中举步维艰的德国人小心翼翼地为生存“保持平衡”,警惕着不久之前还是“民族同志”的同胞偷走自己的配额。在“他人即恶狼”意识中,在战争结束的“零点时刻”圆月照耀下,人狼社会让重新开启的德国历史充斥着不为占领者所闻的低沉嘶吼,走进“狼性时代”。
瓦砾中的狼
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上,都把1945年5月8日或9日视为纳粹崩溃战争结束之日。“零点时刻”这个概念更曾为德国教科书所拥趸,仿佛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德国人便踏入了和平的伊甸园。然而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统治哪怕在联邦德国成立后也仍在继续: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惩治民族有害分子条例》(VergehengegendieVolksschädlingsverordnung)所处的判决,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得到占领者平反——纳粹为维持战争所要求的稳定,与战胜者为维持占领所要求的稳定异曲同工。在企业康采恩总部、大学课堂和国家机关里,纳粹精英依旧活跃在各种工作岗位上,甚至只是简单划去了希特勒授予的头衔。
在纳粹的制度瓦砾之外,更直观的是现实中的瓦砾。战争在德国留下了大约五亿立方的瓦砾,足以把长宽各三百米的齐柏林广场(Zeppelinfeld)堆成四千米的高山。仅柏林五千五百万方的废墟,便足以从柏林到科隆建起一堵宽三十米高五米的围墙,让未来的柏林墙汗颜。在“恢复秩序”的口号下,清理瓦砾成了各地大张旗鼓体现战后新气象的要务。被惩戒的纳粹组织成员,为了一盘热汤的难民充斥在清理瓦砾的工人之中。由于战后男性劳动力的缺乏,柏林清理高峰期有两万六千名女性参与,男性劳工反而只有九千人。渐渐地,“瓦砾女神”作为一道新颖的风景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看到的是与城市废墟对比鲜明的时装女性——最美的衣服总能被女性保存到最后,战后混乱中作为重要财物随身穿戴也就不奇怪了。这些时装丽人在废墟上排队,手把手传递铁皮桶的画面获得了相机的青睐,却越来越远离事实。不但优雅的衣着是摆拍的道具,甚至连镜头前体育课般动作娴熟的对象也是女演员。即便真正的“瓦砾女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演员:虽然工资很低,但重体力工作的食物配给卡甚是紧俏。比起最低等配给卡里让人半死不活的每天七克脂肪,在瓦砾中磨洋工显然是明智之举:“她们非常熟练地用慢镜头的速度传递着装满碎砖头的铁皮桶,让我觉得她们好像确切计算出了最低工作速度,好以这速度完成工作,为自己不多不少地挣得每小时七十二芬尼的工资。”(32页)为了方便,“瓦砾女神”们甚至把碎石直接丢进就近的地铁通道,使得人们事后不得不更艰难地择运出来。

战争结束仅三个月后,柏林市政府就叫停了“失去控制的铁皮桶链”,要求清理工作在建筑当局监督下专业地进行。然而,“瓦砾造神”并未停止,1947年的电影《我们头顶的苍穹》引领了“废墟电影”的潮流,城市废墟的视觉冲击、雄伟的奋斗场面、仰角拍摄的领头人物、超人般的使命感与自豪感让全球电影股份公司把瓦砾清理工包装成了战后英雄。可观众们在感动落泪之时,内心却泛起了一丝似曾相识的违和,仿佛那位口若悬河的宣传大师又举起了手中的话筒。
流浪中的狼
停战之时盟军四个占领区七千五百万人里,足有大半人口流落在他们的故土之外。四千万流民里,一千万是俘虏,九百万是在战争中疏散到农村的城里人,八百到一千万刚刚被解放的在押犯人,以及一千二百五十万从德国东部被驱逐而来的难民。这些背井离乡身无长物之人,不得不在异域他乡寻求安身之所。对于最危险的投降战俘,西线盟军把一百万人圈禁在露天的莱茵大营里,在上无片瓦的铁丝网后任由风吹雨打,忍饥挨饿,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人道主义灾难。
然而,那些在战后社会中逡巡不定的人并不见得幸运,没有人会欢迎他们到来,消耗本就额定的房屋和配给。战前西部德国每平方公里生活一百六十人,在百分之四十五房屋被炸毁的战后达到两百人。居无定所带来了犯罪流行:当时警察记录的抢劫就上升了百分之八百,鉴于大多数人觉得报案也没用,这个比率恐怕要比实际低得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恢复的联邦德国大肆鼓吹“接纳奇迹”,声称正是对一千二百余万被驱逐者的接纳成就了西德的人口与发展。然而,却是盟国“移民委员会”用占领军的机枪才把这些流离失所者送进安置之地的。“融合奇迹”的假象,背后是对自己同胞不下于纳粹的恶毒种族攻讦:“瘦巴巴的吉卜赛人”“波兰来的穷鬼”“东普鲁士杂种”“希特勒的客人”……德国人开始把聚集在新居住区里的被驱逐者叫做“茅茅”(Mau-Mau),亦即外国人聚集的飞地。这个词语标志着德国人对彼此感到陌生,哪怕他们曾经同是“民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战后短短几年,在迁徙流浪中,德国人从纳粹主义下追捧的狂热民族团体,变成了互相呲牙的排外族群。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这种陌生和失望更加具体。无数德国母亲都有同样的故事:她们的男人是如何多年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拿着张退役证仿佛必须向妻儿证明自己是谁。这些流浪归来者的典型就是坏脾气且不知感恩的病残汉子,任由习惯了后方困顿的妻儿苦苦操持家庭,在哀嚎战争伤痛的同时懒散地躺着叫骂折磨自己的家人。“一种集体性的失望正在女人们的内心深处散播着……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除了许多其他失败外,还有男人作为一种性别的失败。”(136-137页)可是,尽管这场战争是男人造成的观点已经成为德国女性的基本信念,但她们当年对希特勒的崇拜并不逊色。德国男性已经成了在战场上迷失了自我的孤狼,而在1945年的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又何尝不是在战后“贪恋生活、渴望爱情”的口号下,在“六女争一男”“女性过剩”的现实中迷失了自己?恰恰是在占领状态开始稳定的情况下,女性间的不信任潜滋暗长,争夺占领者的青睐,互揭战时的老底已是常态,甚至连阵亡军人的寡妇也被视为抢走别人老公的嫌疑犯。
饥寒中的狼
从1939年以来,德国人就已习惯了生活在配给制的桎梏之中,因此1945年配给票证的颁发一开始似乎是福音——作为“生存准许”(Lenbensberechtigungs-Ausweis),它给战败者一种即便在投降后也握有生存权书面证书的安全感。但这种虚无的安全感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当今不少未经历过配给制的人之所以会对票证配给推崇备至,甚至将其作为某种“社会公平”的体现,主要就是误以为票证上的物资是有保证的。但事实上,在配给管制的公平逻辑中,票证定量其实是最高限量,而往下反而没有底线。即便在美英占区,每人也只能获得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热量的食物,仅占一个成人每日所需热量的百分之六十五。且这样的标准也在战后困顿中被大幅削减,法占区甚至传出了占领者蓄意要将德国人饿死的谣言,引来了美国前总统胡佛领衔的国际调查团。1946-1947年百年不遇的寒冬里,一个普通消费者一天的食品只有半咖啡勺糖、指甲大小的脂肪、半根火柴大的奶酪、橡皮大小的肉,一口牛奶和两个土豆。未来的联邦总统阿登纳就此坦言:“在今天的德国,社会地位的差异已经几乎消失。唯有一个区别,那就是能否自给自足。”(190页)
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搏斗。活下来的德国人事实上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人狼”(193页)。法治观念分崩离析,道德传统抛诸脑后,抢劫偷窃成为了心照不宣的惯常做法。在1946年这个饥饿之冬,连科隆红衣主教约瑟夫·弗林斯(JosefFrings)都在年终布道中化去了“汝不可偷窃”的圣训:“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时代,一个人如果无法通过工作或请求以及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维持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物品,那他可以用变通方式来获取。”(194页)主教的训诫马上得到了心领神会的响应,动词形式的“弗林森”(Fringsen)迅速成了一种委婉表达。而红衣主教自己也在英方占领者的搜查中被发现囤了许多“弗林森”来的煤。诚如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öll)所言:“没挨过冻的人,都曾偷窃过。”(197页)
饥寒之下的狼为了苟活,甚至不惜出卖昔日的獠牙。《我的奋斗》、SS徽章……这些在1945年5月带着会吃占领军枪子儿的东西,迅速成了盟军士兵争相收藏的纪念品。当黑人士兵买下一尊希特勒像,而德国卖家感恩戴德地收下三板换来的巧克力时,去纳粹化的光芒达到了顶峰,比任何调查表或演讲布道更加有效。1946年底,恩岑斯贝格尔给美国驻军当了翻译,美军撤走后又改向英军服务。这个爱跟人用英语交流的十六岁少年在“用幸运牌香烟兑换纳粹徽章”的生意中发了大财,十一年后他的诗歌集《为狼而辩》(VerteidigungderWölfe)一夜成名,抨击那些“不愿学习,而将思维留给狼”的小人物。“成功的狼”摆脱饥寒,在一个全新舞台展现自己。
黑市中的狼
如果说战后的德国存在一片应许之地,那就是黑市:战争的赢家和输家,受害者和犯罪者,为了尽量做一笔双赢买卖,都在这一非法领域平等相遇。人们为了交换将身体当作柜台,以暴露狂般的猥亵姿势把大衣打开,对素不相识的来客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的一切。
如果说战后的德国存在一片黑暗森林,那也是黑市:人造黄油中掺着车辆润滑油,袋装土豆里有压秤的石头,不能食用的漆木油被当作食用油出售,而珍贵的烧酒很可能来自某个医学院或博物馆浸过死胎的标本瓶。黑市上的彼此互坑,逼迫后来的联邦德国建立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名义委任机构评测一切商品的消费者组织——商品(货物)测评基金会(StiftungWarentest)。
单单在柏林就有六十个黑市,从亚历山大广场到红灯区,柏林至少有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商品流通经非法黑市达成。成捆的香烟代替不断贬值的货币,成为黑市上的硬通货。黑市商人身体溜圆,轻松愉快地在电车上点燃一支馨香的雪茄,与身边面黄肌瘦,嘬着从占领军脚下捡来的烟屁的同胞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黑市这片战后丛林里,无规则化“奖励了狡猾之人并惩罚了软弱者……在那里显然人再次成为了他人的狼”。在战后配给制人均配给量理性而贫乏的分配映衬下,黑市原始市场力量的野性博弈让德国人意乱情迷,沉醉其中。短短几年的黑市确保了“社会市场经济”成为联邦德国世代效忠的信条。而这一体制之父,联邦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第二任总理,经济腾飞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Erhard)的厚实身板与粗大雪茄,仿佛正是那片战后丛林中志得意满的狼的缩影。
工厂中的狼
一直到六十年代,每辆大众汽车都在引擎盖上带着一匹狼。沃尔夫斯堡(Wolfsburg)的法律规定,每辆这里出产的甲壳虫都有它的市徽“一只金色的,长着蓝色舌头的,回眸凝视的狼”(224页)。然而这个看似有着古老纹章的地方,却是个1938年才出现在地图上的全新城市。5月26日耶稣升天节的奠基仪式上,心血来潮的希特勒承诺要给六百至七百万雅利安家庭提供一部便宜可靠的汽车,“机动车不再是一种划分阶级的工具,它将是大众的公共交通工具”(226页),并重操旧业绘制了甲壳虫形状的图纸。全德国的买家将在德意志劳工阵线“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精心安排下,享受着旅游般的住宿餐饮,一边参观第三帝国最强大的工业心脏,一边满足地把这款德国版福特T型车从这个德国正中心的汽车之城,通过纳粹政府铺设的高速公路开向全国。
然而恰如希特勒的诸多承诺一般,大众甲壳虫最终也只是画饼充饥。三十三万六千人参加了融资计划,却只有六百三十辆汽车交付,甚至在纳粹败亡的战后都没能收回当初付给大众公司的预付款。但纳粹工厂本身却得到了延续乃至关照,成了城市的一切:1943年时,有一万强迫劳工在这个名为“力量来自欢乐”的汽车城工作,占到企业职工三分之二;战后的1945-1948年,新雇人员和解雇人员的数量分别是全部人力资源的三倍。如果柏林是普鲁士的巴比伦,德累斯顿是第三帝国的索多玛,这里就是第二共和国的蛾摩拉。无家可归的退伍兵、流浪失根的男青年,不愿回国的外籍劳工构成了一个似乎停在纳粹时代的孤僻男子集中营。“在沃尔夫斯堡,爱情没有栖身之处”——《明镜》周刊做出了无奈的总结。
即便到西德建立后的五十年代,纳粹痕迹仍深深刻在工厂各个角落。被尊称为“诺德霍夫国王”的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Nordhoff)掌管着这里。他称呼工人为“工友”,属下则称其为“总司令”——其虽并非纳粹党员,却因为经营欧宝汽车厂为国防军生产卡车,有着“第三帝国国防经济领袖”的头衔。1955年,第一百万辆甲壳虫开出厂房,诺德霍夫让全体员工共同为此拍集体照纪念。在照片里的他高高在上,恍如引领狼群的头狼,让人不禁联想起不久之前这片土地的奠基人。
狼之影
魔王覆灭,狼影依旧。
哈拉尔德·耶纳引用了“压抑”(Verdrängung)一词来解释“狼性”的来源。长久以来压迫性国家秩序的崩溃,让许多德国人有了思如泉涌般创造意义的自由和热情,但也使得将德国人的苦难尽可能地高置于其他民族苦难之上的想法泛滥成灾。战后吃了苦的德国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求生本能屏蔽了罪恶感,也使得救赎无关紧要,让他们免去了对真正受害者的思考。战后回到德国的汉娜·阿伦特发现,每当她向人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时,德国人的滔滔不绝会瞬间卡壳:“通常接下来会有一个短暂的尴尬。”但德国人接下来并不会提出“您离开德国后去了哪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这类同情关心的话语,反而往往是一长串关于德国人也吃了多少苦头的叙述(336页)。
同样一幕出现在纽伦堡法庭之外。盟国记者抱怨道:“普通德国人对纽伦堡审判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度的无动于衷……德国人最希望的就是纽伦堡的盟国们来个快刀斩乱麻……但实际上,这只说明当年纳粹统治下的军事紧急法庭和人民法庭的精髓直到现在仍然盛行,这其实是个可悲的胜利。”(345页)在非纳粹化运动中,建立了五百四十五个陪审法庭对九十多万人进行审判,最终却仅有两万五千名纳粹分子认定有罪,其中仅一千六百六十七名是“主要责任者”。
战后大多数德国人集体同意将自己视为希特勒的受害者,这对于数百万被屠杀的受难者而言是难以承受的狂妄,但德国人依然旁若无人地自我接受。这在社会学中被称为“受害者角色的自我认定”(Selbstviktimisierung),即以无以复加的言辞互相冠以的受害者命运,让大多数德国人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直面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纳粹罪行。
1950年,以勇敢反抗纳粹著称的阿登纳任命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的种族主义法学家汉斯·格布洛克(HansGlobke)为总理府主任,并解释道:“除非你有干净的水,否则你不能把脏水倒掉。”
1949年“联邦大赦”(Bundesamnestie),1950年“结束去纳粹化动议”,1951年关于“被解职公务员重返社会”法案,1954年第二部大赦法出台。结束过去的意愿如此深入人心,以致联邦议院成立后一步又一步地消除着盟国占领时代去纳粹化运动的影响。诚然,缺乏“净水”那“脏水”不能倒掉,但这些动议和法律将大多数纳粹凶手免于法律责任的象征意义并不会因此减弱;而且反过来看,这何尝不是意味着真正的“净水”并不存在?
1965年,苏联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执导的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上映。
直到最近二十年,通过格茨·阿利(GötzAly)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HitlersVolksstaat)一书,“正是那些平凡至极的德国人集体造就了纳粹主义”这一观点才在西方被广泛接受。
在战后岁月里,德国政治人物的诸多言谈中,透露着对以往历史自我反思的公开自豪,沾沾自喜地自诩为道德领先者。德国将自己视为“在处理过去的领域里的世界出口冠军”(360页),甚至不再满足于“受害者”的自我认定。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furpolitischeBildung)的网页上这样写着:“最迟至2005年,统一的德国在历史回顾中一跃升为‘二战’的胜利之国。在庆祝诺曼底登陆日以及战胜希特勒第三帝国六十周年之际,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Schroder)及其随行代表团不再需要在庆祝活动中躲躲藏藏。德国政府代表得以出席前盟军的庆祝活动,使成功的德国民主制度受到了加冕般的殊荣。”在俄乌冲突中,重新武装的德国与昔日的东欧“盟友”在过去的“东线”并肩而立,仿佛坐实了“二战胜利者”的新自我定位;在巴以冲突里,朔尔茨的讲稿充满了吸取屠犹的历史教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陈词滥调,但却对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屠杀视若无睹。
尼采说:“人是一根绳索,架于超人与禽兽之间。”哈拉尔德·耶纳作为一个德国人,婉转地把“狼性时代”限定在1945-1955年,将这个时期为生存无所不用其极的同胞比为“狼”,暗示温驯的羊皮之下,“人狼”构成的社会仍在影响日后的德国。但在我看来,1947年时在德国定居考察过的法国学者埃蒂安·吉尔松(EtienneGilson)作为第三方观察者的判断更具说服力,他将战后充满机会主义倾向的德国人比作“变色龙”(lescaméléons):
关于德国人,他们若有十五天是民主主义的人民,另十五天就可以轻易地变成纳粹。你只要看一眼就能确信了。当下每个占区的德国人就已经明显地靠近各自的占领者了……不要忘记即使德国人表现出令人不安的模仿能力,那也只是变色龙在变化外皮而已。
那么,狼或变色龙的故事,今天又到哪一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