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人情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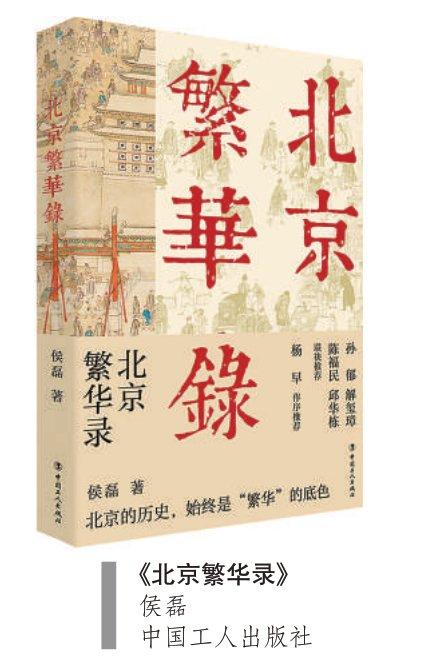
▌赵慕宇
宋代孟元老著有一部《东京梦华录》,细致地描绘了北宋故都开封城的大事小情,书写着对繁华都市的独家记忆。此刻,我手边的新书《北京繁华录》,恍惚间也给人以相似之感——那种对某个城市深入肌理的情感,透过知识与回忆,凝练于一篇篇文章之中。
作者侯磊说:“为了留住北京这个城市的身影,我写作了《北京烟树》;为了追溯这个城市历史文化的细微之处,我写作了《北京繁华录》。”他将自己对文物、文献、文人的关注,形容为“三重门,三重爱”。在我看来,侯磊对故乡北京的爱,不仅是一种回忆式的亲近,更是充满智性的观察与思索。本书描摹北京但不囿于北京,更是对传统文化、传统生活的书写。
侯磊关注旧京民众的生活细节,更关注其中透露出的“人情味”。他在分析北京代表作家老舍时,认为老舍有一种平民主义的倾向,也就是对于普罗大众的关怀。虽说老舍笔下的穷苦人,大都有性格缺点与认知局限,但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并不是一味地同情或抱怨,而是更加理解人物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侯磊评价道:“中国古代小说,都是读书人写市井;老舍是市井人变成读书人来写市井。他以旁观者的身份,表现出对底层人的悲悯情怀。他始终用平视的视角看市井人。”相比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老舍的视角更倾向于理解众人,而不是启蒙众人。
其实,随着时代发展,新、旧价值观之间,势必存在隔膜,这是老舍在一百年前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一百年后同样要回答的命题。与其质疑,不如多一分“同情之理解”。
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世故,有一层含蓄和体面笼罩其间。比如过去挑担摆摊的小贩,在街面上找地方经营,修鞋匠、剃头匠、卖面人恰好都选在药铺门口,那么,药铺伙计便可以找他们修鞋、剃头、吃面,逢年过节,三家摊位要给药铺送礼,药铺还礼轻,意味着摊子可以继续摆,若是还礼重,则是传递“另找他处”之意。
再比如老字号买卖的伙东制,东家出钱请一位掌柜,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东家对掌柜没有量化考核,整个家族连同掌柜,都依靠这桩买卖“吃饭”,分钱时也并非白纸黑字,很多时候掺杂着人情因素。
侯磊还关注民间文化的发展,或者说传统艺术的渊源与流传。比如昆曲,是古代文人雅士创造的艺术形式,带有“书卷气”,保留了许多近古音韵。侯磊认为:既然庆幸昆曲“存古”的功劳,那就更不应肆意地“创新”、糟改昆曲了。昆曲不适合通俗化、流行化。
过往传统还体现在京剧上,比如京剧舞台由男性扮演旦角(女性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早期剧场只允许男性进入,女性无法看戏,更无法演戏;其次,演员学戏初期,不分男女行当,学到一定程度后,才确定自己最擅长的行当,也就是说,其实演员基本都能胜任生、旦、净、丑的各类角色,只是有一门主攻。从表演角度看,男性身高有优势,舞台呈现更好,且演戏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事,全身行头相当重,男性的体力也能更好支撑。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唱腔优势,男性唱高音醇厚优美,女性音调更高,控制不好就比较尖锐。
再如相声,侯磊认为:相声是一门表演艺术,语言和知识只是其中的组成方面。他举例说刘宝瑞有段相声把清代帝王顺序讲错,但实际上并无影响演出效果。早期相声演员,为生存而“撂地”演出,所谓“刮风减半,下雨全完”,所有的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吸引观众,比如开场小唱、白沙撒字、数来宝、太平歌词、贯口等等,远非简化理解的说、学、逗、唱。
侯磊也关注城市的精神气质,比如谈到王世襄时,他引出了“玩儿”的概念——“这是北京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玩到极致,可称为‘玩家’。玩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出学问,玩出境界,过上一种更为开阔的人生。当玩家最大的花费不是钱,而是时间和用心,因而常常能看到经济不够好的人,最终玩出大成就。”王世襄的《秋虫六忆》,就详细地描写了捉虫、养虫的经历,其中不乏艰辛,但更多的是乐在其中的投入。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习惯以功利主义、工具理性思考问题,万事万物难免落于计算当中。其实,这种集体性的精神状况,极易将生活扁平化、同质化,缺乏个性的追求、纯粹的热爱。“玩儿”的价值观刚好可以作为一种调和,让我们看清人生的本质,不仅是追求人所共知的富裕生活,也有对生命体验的热忱与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