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活人感”?从刘晓庆和大冰翻红讲起 | 编辑部聊天室
160期主持人|尹清露
整理|实习记者覃瑜曦
最近,两位长期被群嘲的名人翻红了,一个是被网友调侃了十几年“丫头教教主”的刘晓庆,另一个是曾被吐槽油腻的作家大冰。刘晓庆被前男友曝婚内出轨、“74岁仍在忙着谈恋爱,有8个男友”的绯闻冲上热搜,网友们并没有谴责她,而是对她在情感方面的松弛感、叛逆洒脱的性格大加赞赏,被萝贝贝评价为“只要精神状态足够领先,就会有被年轻人真正认识的一天”。
大冰也是同样。他在去年还只是网络上的笑料,近日却由于在直播上幽默真诚的表现出圈。在直播中,大冰对寻求帮助的网友一一回复:装修不要找熟人、退休后去哪个城市生活最好、中了彩票千万别创业……大家发现,大冰身上的多重身份“民谣歌手、调酒师、老背包客”并不只是夸夸其谈,而是“真懂”。这位作者看似油腻,实则在精神上站在年轻人这边,比如在连麦中表示,年轻人不想结婚是丧失希望的表现,吃尽红利的70后不应该逼迫儿女结婚。

有趣的是,无论是刘晓庆还是大冰,他们都曾经是过气、不入流的代名词,长期以来被网络奇观化,如今却被重新欣赏甚至捧上神坛,拥有了不少“内疚粉”,这似乎说明网络情绪的水温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两则网络热点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词是“活人感”,许多人觉得刘晓庆的敢爱敢恨在满街打小三的网络舆论中犹如一股清流;大冰也被视为“下沉市场的李诞”,面对网友的来信求助没有说教,而是报以亲切朴实的建议。
01大冰没变,什么变了?
徐鲁青:大冰很喜欢强调“江湖”这个词,他经常说自己是个走江湖的,80后有金庸古龙等各类侠客小说的情结,会觉得有情有义和江湖气是人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冰在书里会写一些现在读来很少见的事情。比如他有个卖毛笔的亲戚,他妈妈跟他说,这个亲戚生活很困难,你出名了,要帮帮他,于是他就直接在书里写:我叔叔是做毛笔的,如果你们想买毛笔,可以去找他,他的微信号是xxx。他还在书里叮嘱,如果要去买的话,不要跟他叔叔说买“大冰同款”,因为那款是叔叔送他的,比较贵,大家买基本款就可以了。
大冰翻红可能是因为他崇尚的江湖气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大冰的一次直播中,有个在河南的男生想自杀,连线了大冰跟他告别,他火的那句是“让我兄弟带你去吃一碗烩面”,还建议他出海去做海员等等。
他以前被嘲笑是因为油腻吧,比较火的一篇文章叫《乖,摸摸头》,情节是他从山东电视台离职后,一个同事小姑娘每年都会给他发四个字“好好的,哥”,他就回“乖,摸摸头”。

《乖,摸摸头》
大冰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2014-9
尹清露:之前大冰被嘲讽就是因为油腻,比如对女性会刻板地叫“丫头”。他的翻红让我发现,性别视角不再是唯一的视角,也不再是大家完全投入注意力的地方,这些评论也不能掩盖大冰人很好、给予了大家情绪价值这件事。
刚刚鲁青说到大冰很注重情感、义气和江湖气,这些在今天是很罕见的,他的直播会让我联想到张雪峰,他们俩都是会坚定地给出一些实用性建议的人。想自杀的男生向大冰求助时,大冰很坚定地让男生立刻出海当海员,不要在陆地上工作;还有一个阿姨向大冰提问退休之后的生活,他给的建议是去西双版纳某地当保洁。我觉得这些建议是很安慰人心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具体、很确切的选项,如果我是那个阿姨,我不去好像都有点愧对大冰这么具体的建议,就算不去那里工作,都会去那里看一下。大冰和张雪峰不太一样的点在于:他的建议保留了一些早年间诗与远方的浪漫,简直是戳到了当代人的痛点,大家既想要一个笃定的东西,又想要被给予情绪价值。
提到大冰列了一串title被嘲讽这件事,他其实也说了,自己原本可以找名人来为自己背书,但是他没有。今天大家听他直播时才发现,其实这些头衔也都不是假的,比如他说自己是“说书人”,他确实故事讲得很好;他说自己会各种技能,他在直播间也的确在指导艺术生、指导别人装修等等。我觉得大冰才是先天搞抽象圣体,搞抽象大概的意思是:我用一种很严肃的语气表达,但其实是在开玩笑,如果别人听不懂我的抽象,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傻,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但当时没人懂大冰的幽默。
董子琪:是不是像加个狗头?
尹清露:对,可惜那时候没有狗头这个符号。
徐鲁青:大冰翻红还有一个原因是平民化。现在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惨,甚至互联网上有点仇富或仇精英的趋向,而大家对大冰的好感就来自于——他很平民化,他跟普通人是站在一起的。网上还说他以前骑摩托车去给山区的读者送书,以及“他不像韩寒和郭敬明直接从文学进入影视大赚特赚”。这些话语和大众对张雪峰的评价有相似性,他们不是那些站在高处的知识分子和精英,而是跟所谓的普通人站在一起的。
尹清露:且不说大冰这样做到底是不是他真实的想法,至少他表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去年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冰学”,今年大冰名声反转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网上有媒体是这样评价的:大冰非常敏锐,他在好的时代紧紧抓住了年轻人看世界的欲望,在坏的时代,又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求安稳的需求。
这段话是很有道理,但我在想,去年“冰学”大火的时候,大众情绪也是想求安稳的,跟今年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去年我读到了一篇关于完颜慧德和大冰抽象笑料的文化评论,谈到大家宣扬“冰学”是出于某种绝望,通过笑料得到短暂又廉价的神经刺激,从而更顺滑地在压力中劳作,但生活本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到底是什么发生变化了?
我最近在读日本学者宇野常宽写的《00年代的想象力》,他提到日本也经历过相似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家有一种退缩、保守的心态,直到后面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仍然很重要。换言之,先前处于没有物语的时代,只需要去消费抽象的笑料。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我们还是需要叙事的,而叙事来自于人的关系性。只不过,现在任何叙事都不稳定,反而是很确定的叙事会让人感觉很好,即使你内心深处并不一定相信它。这就能说明大冰直播间为什么火了,首先他给人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温暖,其次他提供了一些不一定有效但“有用”的建议,也就是各种小叙事。

《00年代的想象力》
[日]宇野常宽著余梦娇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10
02商讨人设,翻转人设
潘文捷:大冰和刘晓庆的反转让我想到美国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提出的“文本盗猎者”这个说法。实际上,大冰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应该关注和评价他的文学作品,刘晓庆作为一个演员,我们应该去评价她的演技和影视作品,但最近的浪潮其实都没有关注这些方面。现在的一种趋势是:网友们的评价与他们的作品本身无关,与他们呈现的自我无关,只与网友给他/她赋予的人设有关。
例如,以前明星或经纪公司会给明星本人安排一个人设,但是粉丝在人设的确定上处于强势地位,可以通过各种文本创作、讨论等数字劳动去建构出他们自己满意的人设。基于此,刘晓庆和大冰最终的形象也未必是他们自己本意要呈现的,而是粉丝或大众商讨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时候,大冰作为一个作家、主持人,刘晓庆作为一个影视从业者,他们也必须面对现在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都得以某种人设来开展自己的工作了。

这种人设就像日本文化学者东浩纪“数据库消费”概念中的萌要素一样,都是通过新的材料、新的我们看到的内容慢慢地叠加的。大家之前觉得大冰的这些title是玩笑,现在发现多少有点真实,那么慢慢地这些title也叠加到他的人设上面去了。通过这种萌要素,进而不断地让大家对过去的印象进行反思,对以前的人设进行重组,从而才会有人设反转、风评反转,所以我感觉,只要在公众眼中保持一定曝光度,你多少都有机会来实现这个反转。
尹清露:人设这一点我也很有感触。我发现大众对“人设不能崩塌”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反而是加固了的,因为大冰和刘晓庆其本身人设并没有变化。正如萝贝贝那篇文章说的,刘晓庆之所以翻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丫头和女皇的人设在绯闻中一点都没有崩。我最近在看《永夜星河》,女主演虞书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开始大家批评她“作”,但逐渐地发现她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后,她的风评和人气也迎来了反转和上升。

除此之外,媒介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过去,刘晓庆只能作为电视明星或者某个角色生活在电视媒介中,大冰则是通过书这一媒介被熟知,而如今已经是《娱乐新闻小史》书中提到的“网红逻辑”了——这本书指出,网红逻辑正在向平民和传统名人两个领域渗透,普通人也要学着用网红的策略获得关注,名人也要使用类似的技巧维持人气,名人已经从遥远的、被遥望的精英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常见部件。
《娱乐新闻小史》作者闫岩还认为,网红逻辑普及前,电视明星是真正被冻结在时间里的人。电视明星和电影明星还有些不同,章子怡作为电影明星,她演的角色都很不一样,所以她的个人性格很鲜明。然而,电视明星只能一直活在人设里,例如《武林外传》中饰演白展堂的沙溢,在此之前他的戏路很广,但饰演白展堂之后,他无论再演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他像白展堂。同样,剧中白展堂的行为也不能超出人设,比如这一集中他有了桃花运或是超出人设外的部分,这类戏剧冲突必须在一集之内被解决。刘晓庆在网红逻辑没有普及之前,可能也一直活在丫头或其他电视剧角色的人设里,但现在这个固定的生态已经变得分散了,她不用以电视剧里的角色示人,而是以真实的自己面对大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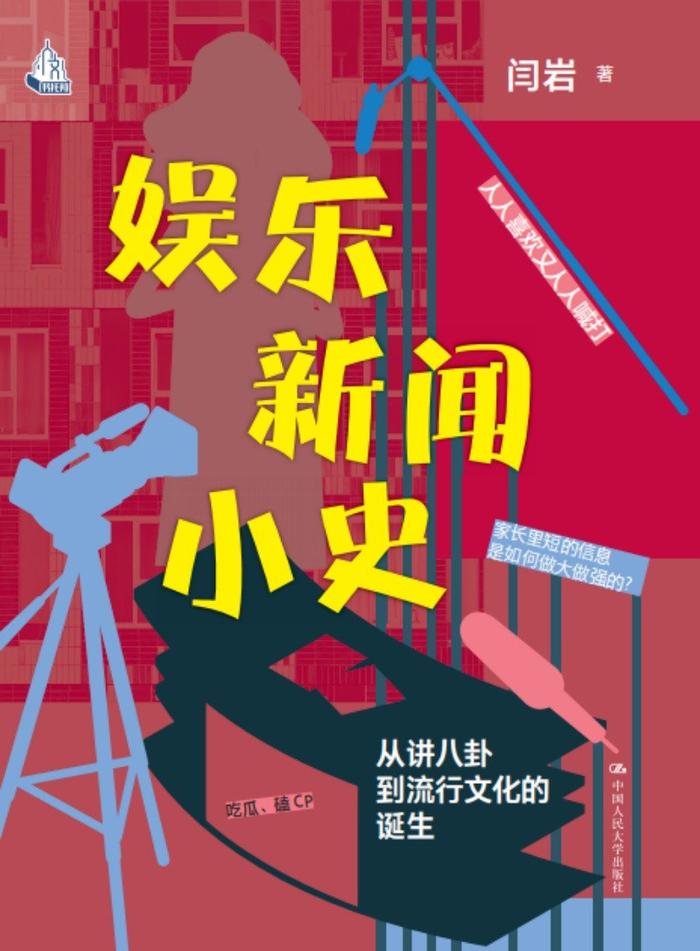
《娱乐新闻小史》
闫岩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4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实际上,刘晓庆的人设并没有发生崩塌。很多人会把刘晓庆和她扮演过的武则天类比。界面文化此前的一篇专访《范冰冰和刘晓庆证明了武曌一直是中国集体想象的一部分|专访汉学家罗汉》提到,早在千年之前,武则天就愿意去“引起一些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去模糊、混淆、挪用、颠覆、篡夺、曲解、再定义、重新组合及重新阐释性别角色及其背后的意义”。这让我想到,刘晓庆的种种事迹也印证了这种“超前性”。同样,大冰那些早年间“混江湖”得到的民间智慧,如今也很受网友的追捧,而他那种浪迹天涯的心态和形象,也在今天变成了宝贵的东西。
03“活人感”、“活人微死”和“死人微活”
董子琪:“活人感”这个词说起来真的好奇怪,人不都是活着的吗?难道还有“死人感”吗?可能是觉得内娱里很多人不那么有个性,没有那么有生命力,所以比较赞赏早期的一些风格等等。这很像是对卢梭的“高贵野蛮人”(noblesavage)的向往,向往着无拘无束的、在社会主流规则之外的、生机勃勃甚至有点粗鲁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刘晓庆传播最广、最受追捧的一个形象,就是她说“日本鬼子暴露我的年龄了”这种爆粗口的女性形象,大家会觉得这种是更加“真”的。
这类形象在现当代中国影视界挺受欢迎的,女性角色中这类形象比较少一些,我能想到的是小燕子、刁蛮公主;男性角色中这类形象比较多,例如《我爱我家》这部剧里,葛优演的季春生就是一个标准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流民,他的形象其实是:身无所傍,满口谎言,甚至蔑视权威、歧视女性,放纵自己的欲望。后来我看葛优无论演什么角色都有“季春生”这个形象的影子在。除此之外,姜文饰演的许多角色,王朔笔下的许多人物(比如90年代电视剧《过把瘾》里王志文的角色)也都有这类形象,会爆粗口,讲一些这个世界的真相,我觉得挺像刚才鲁青说的“江湖气”。

“江湖”可能不是某个代际发明出来的,而是一脉人物所崇尚的规矩,通常来说他们是游民一样的阶层,就像王元化引用过杜亚泉的观点:中国社会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是游民这批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能代表刘晓庆或大冰背后的高贵野蛮人的想象,虽然在这个处境中,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他们仍然显得非常高贵,跟文明虚伪、很多套路、很多规矩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过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粗野如果放大了的话也会让人不堪忍受,所以还是要调和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人觉得喜欢,不管是小燕子还是刘晓庆。我觉得刚才文捷说的“文本盗猎者”也很有道理,不是大冰或刘晓庆他们发生了变化,而是大家文本盗猎的方式和趣味发生了转变。
尹清露:我一开始看到“活人感”这个词,想说是不是跟“出格”差不多?比如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就期待有一个出乎意料的人出现。子琪问难道还有“死人感”吗,我觉得跟“活人感”相对的可能是“人机”。我就是一个经常被吐槽像“人机”的人,比如经常回答“确实”,安慰别人的时候只会说“宝宝你别哭了”、“宝宝我抱抱你,安慰一下你吧”这两句。
或许当技术发展到人可以跟机器对话的时候,其实不仅是机器在模仿人,人也在模仿机器。这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更珍视一些人的出格的、逃逸出去的一些特质。
董子琪:我看过一部刘晓庆和陈佩斯演的王好为导演的电影《瞧这一家子》,她饰演一个售货员,演得非常好。这可能真的跟人的情感容量、个人气质有关系,她就是一个那么小的配角,演一个国营商店里对顾客非常不耐烦的售货员,但是她一直迸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非常有标志性,让人忍不住要看她,就是要围绕着她。那时候刘晓庆还很年轻,远远没有什么女皇特质,但依然很吸引人。

尹清露:还有人说刘晓庆在一部剧里面同时演了8个角,真的很爱演哈哈哈。情感容量这个词还挺对的,她能够容下来这么多情感,所以才能够演绎出不同的人。
潘文捷:不知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两个流行的词汇,“活人微死”和“死人微活”。我之前看了一些“活人微死”的表情包,上面会写“如果世界是个群,那我已经退了”、“原来我是学生,不是畜生”、“没事的,杀不死我的,我会自己死”、“领导说我笨,笑死,聪明可是另外的价钱”等等调侃的内容,感觉现在不论是给老师还是老板打工,大家都是一种“活人微死”的状态,有一种想躺平但不得不被领导“扎一下”让你起来干活的“活人微死”感。“死人微活”就是默认自己已经“死了”,但是看到比如恋综里面甜甜的糖,又会感觉“尸体暖暖的”。这两种状态跟以前一直讨论的“佛系”或者“躺平”也有些关联。
再谈回刘晓庆,她的身上除了活力,还有一种女性身上很少见到的“第一性”的感觉,她没有那种被审视的感觉,好像没有受到父权社会的打压。我还想到那英,她是子琪说的“会爆粗口的女性”,经典语录是“最烦装逼的人”。我今年也看了《歌手》,觉得那英唱得一般而且很老派,乐评人都说她唱得不好,她又很紧张,唱歌也出错,但最后还是拿了冠军——这跟大家很喜欢她有关系,她就是第一性的感觉。
此外我也想问:这只是跟她们的性别有关吗?还是跟她们的阶层有关系?可能到了那个社会阶层,你可以做出很多普通女性做不了的事情,好像既是“野蛮人”但又很高贵。
徐鲁青:刘晓庆对于大多数权力和规则都不在乎,我看了她的书,书里面有一段说:我经历过下乡,还有各种运动,我还进过秦城监狱,但是我现在还是能站在这里。
潘文捷:我想到另一位女演员陈冲,她和刘晓庆一起演过《小花》,她俩的差别很大。陈冲和学者罗新对谈的时候,一直说自己缺乏知识,“我好像不配给大家讲我是一个模范青年”,“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我”,“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她家里人觉得演员不是一个真实的职业,会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要求去要求她。

董子琪:这就是文明(civilized)和野蛮(savage)的对比。
徐鲁青:黄圣依爸妈也是知识分子,她也很代表文明。
潘文捷:她太文明了,所以她就“死人微活”了——黄圣依在《再见爱人4》里就有一种“死感”,很多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徐鲁青: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将知识分子和软弱绑定在一起,这是一个漏洞。以前批斗知识分子的时候会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软弱,就是没有办法坚定地改造世界。大家好像很喜欢把拥有知识和是否软弱、是否容易感到羞耻联系在一起,好像错的是你本身读书读太多。
尹清露:当然,下意识认为知识人软弱,这是一种偏见,也有反智的倾向,但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确实更需要野蛮的东西。很多年前,我们会很温和地用一些理论讲母职,讲男性要更加参与到女性的照护之中,都是很有道理、循循善诱的感觉,可是现在我发现,大家需要的是刘晓庆书中写的“我进入男人社会,操控男人,统治男人”,是要先成为统治阶级、先坐上皇帝的位置再去谈改变的意思。虽然不能完全类比,但美国大选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你是想去听左派那些道貌岸然的空话,还是去右边赌一赌机会。”
潘文捷:权力都是要争夺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果真的要去争夺这个权益的话,过程中讲道理是讲不清楚的。《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这本书就认为,在整体生活能够得到保障的时候,大家的生存安全感都很强的时候,大众会更加倾向于文明地说理;可一旦在生存上面有压力,大众就会希望有一个威权的人来引导。这本书分析了为什么如今美国民众都不再支持左派,因为现在的左派抛弃了原来传统左派阶级斗争的道路,改向了文化上的议题,而尽管美国人从世界视角看来依旧富有,但民众是感觉得到威胁的,包括整体贫富差距的扩大、移民抢了部分人的工作等等,他们自我感知的威胁在增强。
尹清露:所以无论是“活人感”还是“高贵的野蛮”都需要适度,就像是左和右的互相牵制。只不过现在看来,在这个到处都是“活人微死”“死人微活”的时候,大家会更倾向于野蛮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