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法国,阅读让大众更清楚地意识到解放的可能
【编者按】
19世纪,文学第一次对法国下层阶级的成员免费开放。随着数量史无前例的“新读者”加入,阅读大众不断壮大,阅读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进程。本文摘自《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与农民》,[英]马丁·里昂(MartynLyons)著,张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4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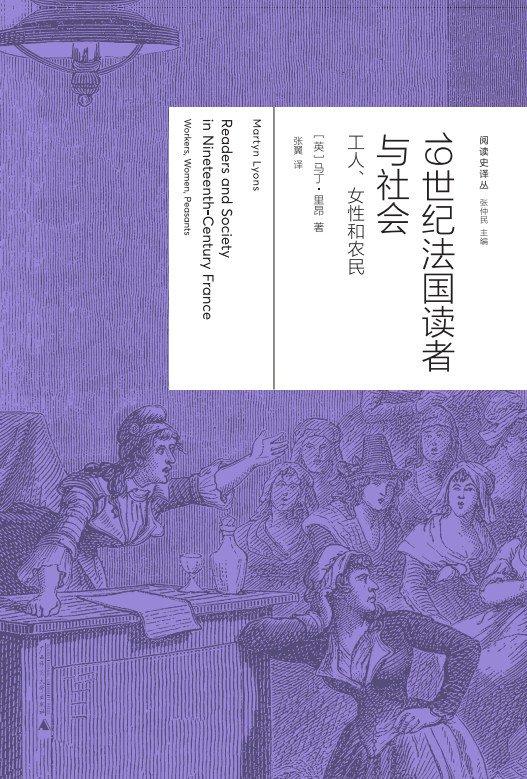
路易·舍瓦利耶将他那本著名的关于19世纪早期巴黎的作品命名为《劳动阶级与危险的阶级》(Classeslaborieusesetclassesdangereuses),这表明在行政部门、当局和作家眼中,工人对于资产阶级文明而言是个威胁。按照同样的风格,本书也可以叫作“阅读阶级与危险的阶级”。它的前提是:在19世纪的法国,工人、妇女和农民的阅读被视为对父权制、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威胁。它同时也是天主教会的焦虑来源之一。在19世纪,文学第一次对下层阶级的成员免费开放。首先,他们可以按小时从阅览室租书。后来,随着卡尔曼-列维、加尼埃(Garnier)、阿谢特和弗拉马里翁等出版商对迅速扩张的市场的开发,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生产成本越来越低。小说在报刊上连载,并以低廉的价格每周或每月分期出版,进一步拓宽了读者群体。从1860年代开始,插图杂志和《小日报》这样的大众流行日报出现了,依托于铁路的新物流手段将它们带到了法国的小镇与农村。随着数量史无前例的“新读者”加入,阅读大众不断壮大。阅读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进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反而试图遏制它,并影响其流向。
资产阶级和牧师的焦虑起伏不定,其症状在19世纪的进程中不断演变。他们对于阅读的恐惧,在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19世纪的后革命时代中变得最为激烈。例如在1815年之后,天主教会对于坏书的攻击,以及推进针对挥之不去的雅各宾主义的文学解药,都是精神上再征服之系统性努力的一部分。1848年革命引发了另一起对于大众阅读的重大警告,不仅是因为1848年6月民众的起义,还因为男性普选权的引入导致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巨大成功。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争论的主题再度转变。随后,大众阅读成为神职人员和自由派共和党人争夺意识形态霸权的竞技场。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大众阅读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对大众阅读的恐惧,既是天主教会对世俗化恐惧的核心,亦是资产阶级对民主化恐惧的核心。与此同时,未经指导的女性阅读挑战了资产阶级父权的基本假设,同时也挖了天主教教士广大女性支持者的墙脚。
我希望阅读史因此能够得到澄清,不再仅仅被当作文学史中一个曲高和寡的分支,而是一个能够阐明一些核心的社会发展的话题。阅读实践的历史与这一时期更广泛的阶级关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为统治阶级试图通过阅读建议和创建适当的文化制度来中和社会冲突。我们已经看到,借阅图书馆在整合小资产阶级方面比整合工人阶级更成功——此处借阅图书馆的故事就像是第三共和国历史的缩影。
我也希望阅读实践的历史能够揭示出19世纪性别关系的一些方面。男性小说家、天主教徒和女性主义者为女性提出的阅读模式表明了性别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各种对女性读者的再现相互竞争,但它们似乎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它们都认为女性读者特别倾向于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文学挪用方式。因此,女性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浪漫低俗小说的邪恶影响。
阅读实践的历史与其他关于社会对立和性别表征的历史以这些方式交织在一起。也许这只在19世纪才成立,因为印刷文化在1914年之前的这个世纪中变得愈发重要。印刷文化在当时已经普遍识字的人群中获得了大量受众,而且尚未受到广播、电影或任何电子传媒的挑战。印刷品在这个短暂的历史时刻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使用印刷品的辩论,就是对社会本身的性质与工作方式的辩论。
我非常清楚,本书介绍的故事并不完整。有一处疏漏值得强调。我没有更全面地讨论法国的教育制度。显然,介绍茹费理的教育改革是对这里所讨论的共和主义的问题最成功的解答之一。全新的国立小学和其中近乎教士一般的男女教师,开始塑造一种建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忠诚之上的民族意识。但是,全面描述19世纪学校阅读经验超出了阅读史的范围。其他历史学家已经研究过它,而阅读实践史是这一领域的相对新来者。我之所以选择把重点放在成人而非儿童读者身上,是因为我相信,最早在1880年代以前,许多新读者只短暂而断断续续地上过学,他们的学生时代是在教室之外度过的。
没有读者的历史,就没有阅读实践的历史。同样,没有读者的历史,文学史也不可能完整。我们要让他们不仅仅是小说家想象中虚无缥缈的受众,不仅仅是牧师谩骂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图书管理员手上没有面孔的统计数据中的条目。我们需要接触读者个人,认识到他们作为人的存在,欣赏他们阅读体验的多样性。有时,他们的阅读策略吸收了阅读模式和建议的元素,这些模式和建议镶嵌在19世纪关于阅读的论述之中。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学文化。他们个人的故事对于理解过去社会中的阅读不可或缺。欧仁妮·德·介朗、埃莱娜·勒格罗、文盲的诺贝尔·特鲁昆,还有安妮-玛丽·蒂耶斯采访的阿尔岱什省女性,他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我们的分析依赖于他们,没有他们的陪伴,我们的历史旅程将是无聊和单向度的。
我们可以从这些读者的信件、日记和采访,以及最重要的,书面自传中了解他们的故事。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提防这些资料。他们可以捏造细节,审查不符合自己理想版本的内容,或者向公众展示一个高度修剪过的形象。激进分子的回忆录可以被用来构建颂扬无产阶级斗争的殉道学。对农村生活的追忆可能充满了一种对于法国真正的乡村根基的“农民主义的”怀旧之情,而自1950年代以来,新的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导致这种农村根基的逐渐消亡强化了这一情感倾向。所有自传都是虚构的,它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作者是如何再现自己及其阅读的,而非他们实际阅读的内容。但他们如何把自己“想象”成读者,这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自传的流行满足了怀旧的商业需求,但它也有更深刻的政治含义。通过摆脱赤贫而“发家致富”的工人的生活故事可以被右翼分子用来动员新人。根据撒切尔主义者对他们作品的解读,它们宣扬了诸如自助等19世纪价值观的持久相关性。更重要的是,这类自传成功地将贫困本身历史化了。它们把困苦和物质匮乏牢固地置于我们如今已经摆脱了的泛黄的过去中。饥饿、恶劣的住房条件和暴虐的雇主似乎是早期工业革命的遗迹。因此,工人阶级的自传被用来让贫困显得很遥远,让福利制度显得很过时。
然而,通常情况下,这里讨论的19世纪自传并不是为了促进维多利亚式价值观在20世纪复兴而出版的。大部分作品出现在作者生前。它们大多在巴黎以书籍的形式,或者在当地的杂志上出版。如果阿古利科·佩迪吉耶的例子靠得住的话,那么出版常常很困难。他第一次试图出版《学徒回忆录》(Mémoiresd'uncompagnon)时被新闻出版社(LaPresse)拒绝,编辑吉拉尔丹(Girardin)告知他作品没什么意思。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时,印量只有500册。女性面临着更大的障碍。19世纪的出版业并不欢迎独立的女性作家。女性的自传写作只有靠男性中间人的介入才得见天日。比如,玛格丽特·奥杜(MargueriteAudoux)就是在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Mirbeau)的推荐下被“发现”并出版的。然而,这类赞助者并不总是完全欣赏他们的女门徒。女裁缝兼工会主义者珍妮·布维耶的手稿遭到了删减,但她天真地将这种删减视作褒奖,因为从未觉得自己有能力写出足够一本书的材料,她自豪地说:“我原本以为自己写不成书,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创作,我超出了篇幅限制。”口述的自传同样要经历中介:采访中的动力关系和采访者的问题与优先级。遗憾的是一些采访者并没有公布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许这是为了抹去自己在信息收集过程中的存在,他们希望给人一种超然的错觉。采访者的消失把戏不应让我们误以为信息提供者的声音是纯粹自发、未经编辑的证词。然而,尽管口述证词充满了各种政治倾向的陷阱、怀旧之情以及透明度的幻觉,如果阅读史想要有人性的一面,我们就还是必须抓住这些自传材料。
读者会承受各种社会和文化压力。尽管如此,任何个体的反应仍存有不可忽略的自主性。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常常共谋破坏了作者的意图、牧师的警告,或者出版社竖起的微妙提示。一个人可能会为了颠覆其权威而阅读正典,或者为了更好地反驳而阅读无神论小册子。一旦考虑读者反应的问题,我们必须为一些意外做好准备。然而,读者个人从来都不是完全自主的。在布尔迪厄的概念中,他们的个体性受其文化和经济资本的限制。换句话说,一方面是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教育资格,二者将读者置于不同的类别之中,其文化实践符合可辨识的社会学模式。因此,他们的阅读是一种共同习惯的表现,就像那些自学成才工人的阅读,也是节俭、社会抱负以及与身边那些常常醉酒的广大工人保持距离的习惯的一部分。这些读者在共同的语境中阅读写作。他们认为缺乏教育机会是压迫的根源。他们对阅读的渴望反映了想要超越现状的个人抱负,但这也让他们对社会不平等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不一定接受过形塑了西欧中产阶级的古典教育。用布尔迪厄的话说,他们并不熟悉19世纪中产阶级所继承的“文化资本”,尽管其中许多人渴望宣称自己分享了这种文化遗产。这群杰出的工人阶级读者组成了一个非正式读者社区,因共同的反教权主义而团结在一起,对什么才是好文学有着相似的看法。
这里所讨论的“新读者”使用了不同的挪用方法。自学成才的工人认为自己的阅读具有解放性。“让我们打碎我们的偶像”(Brisonsnosidoles),正如阿尔诺在启蒙时代的修辞中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粉碎我们的偶像,进而只考虑我们共同的福祉;让我们阅读让-雅克·卢梭;让我们阅读拉梅内、维克多·雨果和夏多布里昂;这些人将唤醒我们的灵魂,澄清我们的判断”。农民的阅读更为务实。他们会寻找实践的、有用的信息,要么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要么能让他们完全离开土地。本书选择研究的女性读者更看重小说,更喜欢与文本有情感或精神上的联系。作为个人和非正式阅读团体的成员,她们参与了整个19世纪争取独立和自治的斗争。工人寻求自我解放和一种自给自足的工人阶级阅读文化;女性读者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不受男性审查和家庭监护。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阅读可以让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解放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