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孤岛上自得其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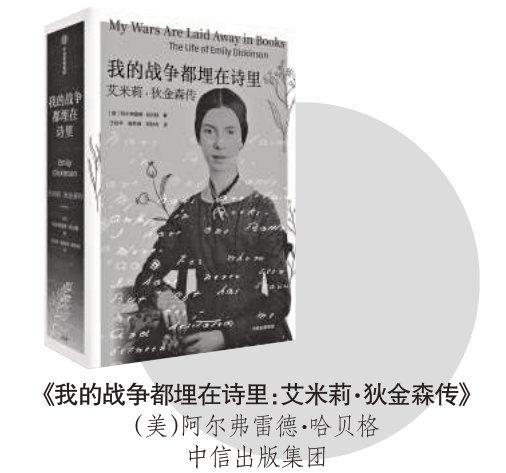
▌董琳
关于艾米莉·狄金森,我们知道些什么?
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很难理解她诗歌中深邃的含义。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她写了两千多首诗歌却几乎从未发表。我们更难理解,一个把“宅文化”演绎到登峰造极的神秘女诗人为何会有如此魅力,令人读过她的诗后,只想进一步探索她的平生。
她的诗带着神秘、叛逆、令人无限遐想的风格。读狄金森的诗,你或许会摸不着头脑,但你一定会沉溺于文字本身的魅力而无法自拔。抽象又真实,普遍又特殊,狄金森的诗歌里有着无限的窗口,每一扇窗口都为你留下一道神秘的路径,显然是在召唤你无穷地探索。
作为比肩惠特曼的诗人,狄金森的一生似乎应该是为人熟知的、精彩的,甚至是带着诸多八卦花边新闻的,但她却把自己装进了搭建好的房间中,隐士是对她最好的称呼。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的一生,又令多少读者都为之神往又好奇。《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艾米莉·狄金森传》的作者哈贝格为了写下、写好狄金森的传记,辞去了工作,卖掉了房子,穷其精力,撰写出了狄金森错综复杂又神秘的一生。
从25岁之后,狄金森就开启了独居生活,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并在岛上自得其乐。她像是那个时代的旁观者,驾一叶扁舟,抛弃同时代人于千里之外。在别人不断向外探索时,她选择向内探索,去想象死亡,思考死亡,从年轻到暮年,持续地书写死亡。她都是直接的、全然的、纯粹的“向内”写作,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部世界的象征物。
狄金森毫不畏惧地面对死亡,不放过其中任何犄角旮旯,通过一层又一层渴望又恐惧、谦恭又反叛的探究,她也创造了自己,并且以她惯用的悖论方式描画出死亡的反面——生命——的生动肖像。
她的文字是跳脱、叛逆、不拘规则的,狄金森对词序的任意颠倒,是读者面临的极大挑战,完全不相干的元素,像用魔法融合在一起。但内在里,词语们又像谜语和星辰那般呼应甚至对立。她的诗句情感浓烈而压抑,措辞如同藏在珠宝盒里的炸药,我不得不将目光移开,以免被灿烂的火花灼伤了眼睛。而她的信件文辞优美,遣词造句如同诗歌,对她来说,诗歌与信件都是她描摹感觉、传递思考的工具。唯有诗信一体,才能镌刻一个真实的、趋近于完整的艾米莉·狄金森。
狄金森曾给苏珊写过一些最为热情洋溢的信:“清早的花朵,惬意地享受晨露的甘美,然而,也仍是那些花儿,正午时分却在强烈的阳光下痛苦地垂下脑袋,想一想,你们这些干渴的花朵,此时除了露珠就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吗?不,尽管会被灼伤,被烤焦,她们也会渴求阳光,渴望火热的正午,她们已平静地接受了——她们知道,正午的男人比清早更强大,她们的生活从此要随了他。啊,苏西,这太危险了。”
狄金森终生未婚,哪怕她把“Master”视作她的灵魂伴侣与人生导师。弗吉尼亚·伍尔夫感慨,在西方传统的社会中,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女子要想成为作家、诗人是难上加难的。在那个时代,女子的首要任务便是作为生育工具,使家族的血脉得以接续下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极不对等,女性被家庭这个镣铐限制着,结婚生子养育就是她们三十岁后的所有事务。狄金森看到太多伴侣的分分合合,令她对妻子这个符号惶恐不安,害怕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附属品。当她把爱情看得更为明白的时候,她决计不再让自己为任何人保留一种从属的地位。
狄金森具有的开拓精神,处处体现着反抗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她几乎未曾离开过家宅那一方土地,却创造出了宝贵的文学财富,这便得益于她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虽然未曾见过外面的世界,但书籍帮她解决了这一难题,她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在自己的圆桌上进行创作,这是多么宁静且难得的写作环境,而这正是伍尔夫所强调的“房间”的一种。
狄金森是一名基督教徒,信仰是她创作的神圣感来源之一。她曾说:“信仰本身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在它的沉重下蹒跚前进,但却始终放不下它。”16岁时,她写信给好友爱比亚,问:“你不觉得永恒很恐怖吗?”“我几乎要接受‘他(耶稣基督)在我之上’的说法。每日活在基督的慷慨里,却仍对他与他的道怀有敌意,我是多么不知感恩。”由此可见,狄金森一方面敬畏基督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她又怀疑这种毫不反思盲目集体崇拜的教义,由此看出对于宗教,狄金森并不坚定。
于她,最信奉并坚持的始终只有文字。她用最虔诚的态度来对待写作。她曾这样形容夜晚写诗的经历:“晚餐后,我躲进诗里,它是苦闷时刻的救赎。一旦完成一首诗,我觉得放下了一个负担。晚上诗行常会吵醒我,韵脚在我脑中走动着,文字占领我的心。接着,我就知道世界不知道的,那是爱的另一个名字。”
狄金森的诗歌像是棋子,随意组合,没有章法,但突然间却可以变成壮阔而雄伟的军队,可以变成辽远而神秘的幽深。一个时代的旁观者,一个隐居于世外的女子,思想却可以超越时代,穿行于自然与人心之间,她带着悲悯与忧愁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诗歌。《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艾米莉·狄金森传》不仅是阅读狄金森诗歌的指南,更多的意义在于“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效果近乎一次复活了狄金森的举动。
狄金森的诗歌真的很好吗?这似乎是个伪命题。生前她只发表过十首诗歌(一说七首),部分发表在《共和国报》,但大多经过遵循传统语法规范的编辑修改,折损了原貌。而她如卡夫卡一般要求烧掉她所有诗歌的遗命,也幸而同样未被执行。经过亲友的整理、结集、出版,狄金森的诗才逐渐被文学界关注,成为被主流认可的杰出诗人,与惠特曼、T.S艾略特、华莱士·史蒂文斯、布罗茨基等诗人并列在文学的万神殿里。到如今,狄金森的地位已很少有人质疑,她的诗歌也深刻影响了伊丽莎白·毕肖普、露易丝·格丽克等美国后辈。
狄金森通过其独特的诗歌创作,深入探讨了生命、自然、爱情、死亡等主题,展现了她独特的人生哲学。她的诗歌风格凝练、意象独特、语言精微、思想幽深,充满趣味,极具先锋性,似乎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甚至带着那么点另类。但也正是这向内的、自我的、神秘的、不被韵律束缚的狄金森,会让你感动、深思。可以说,狄金森凭借一己之力开创了新的风格,令现代诗歌多了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只是这些,都不是百年前离开的诗人所能感受到的,终其一生,不过是漫长、孤寂,以及长夜中每一个微弱但虔诚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