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答法国汉学家索尼娅问:如何在变形的世界中沉思?
转自:上观新闻

赵丽宏的诗集《变形》十月即将推出法语版本,并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面世。《变形》中的60余首诗歌作品,不仅揭示了人性的深度,亦包含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广度,也成为中法交流的一种方式。
就此诗集在法国的出版,赵丽宏与法国汉学家、哲学家索尼娅·布雷斯勒进行了对谈,对诗歌当下的可能性和未来的敞开性进行了真切的交流。

■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的
索尼娅:您的诗集名为《变形》,这个标题唤起了一种持续的转变,能否谈谈这一概念在您的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
赵丽宏: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不同的人的视野中,世界变化的形态也许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周围事物发生的变化极其敏感,也有人视而不见。世界的变化,其实也是人的变化、人的观念的变化,人对历史的认知、对现实的判断、对未来的憧憬的变化,引起他们心目中的外在天地的变化。
我的很多诗作,都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这样的描述,也许非常主观,是一孔之见,是有别于常人的妄想和幻觉,但对描述者来说,是真实的。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恒定不变的事物,但这些不变,大多是精神的产物,譬如心中的某些执念。我一直希望自己“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不管周围的现实如何喧嚣,保持心绪的宁静、坚守自己的目标、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虚伪、不媚俗。我曾经用“礁石”作为自己在网上的笔名,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想法。礁石在海中,经受汹涌的海浪永无休止地冲击,但它永远以不变的姿态屹立着。但浪中的礁石其实也在变,海浪的冲击和腐蚀,在它的身上留下了痕迹,那是在远处无法看清的累累伤痕。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索尼娅:本诗集中许多诗歌探讨了记忆、时间和变形等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反映在您的个人生活体验中?
赵丽宏:记忆这个词,涵盖了过往的所有时光和经历。不管是清晰的往事还是模糊的印象,不管是轰轰烈烈的事件还是幽光闪烁的瞬间,都是记忆。我的大多数诗作,都和记忆有关,在我的诗中,它们展现的也许是一段往事,一个人物,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一段音乐,一件器物,一丝微笑,一滴眼泪……在沉思时,在旅途中,在梦境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叩响我的思想和情感之门,给我写诗的灵感。而所有这一切与记忆有关的诗句,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时间。时间笼罩着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也许还有另一个主题——变形。记忆中的景象,经过时间的酝酿,重现在诗句中时,已经面目全非。
■我的文字,还是发出了声音
索尼娅:在诗集《变形》中,诗歌《此生》讨论了痛苦与快乐、斗争与追求的二元性。您如何看待这种二元性在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赵丽宏:《此生》这首诗,其实是对人生的反思、对生命的反思。我近年的很多诗作,都是在作这样的反思。回溯生命的过来之路,有迷惘忧伤、有苦痛哀愁,也有欣喜愉悦和欢乐的笑声。那些不同的情绪,在生命中不时交替,也经常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状态中的二元性或者说多元性,它们之间冲突纠缠,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每一个人,让你沉迷,让你困惑,让你惊恐,让你忍不住回头寻找自己的脚印,也不断审视自己的所在之地,并不时自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
索尼娅:在《平衡》这首诗中,您探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这种张力如何影响您的诗歌创作?
赵丽宏:你把这首诗的题目翻译为《平衡》,中文原诗的题目是《天平》。天平,是一种测试轻重平衡的仪器,也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意象。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平衡。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在追求或者希望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平衡,只是一些我们希望抵达的瞬间。而不平衡,却是生活的常态。在诗中,我让自己站在一台天平仪的中心,试图以自己的移动来控制天平两边的平衡,而天平的两边,不是具体的有重量的物件,而是两个无法触摸的抽象概念:过去和未来。使自己成为平衡支点的想法,当然是荒唐的妄想,你再怎样移动位置,也无法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去和未来,每个瞬间都改变着它们的位置,时光的流逝不受人控制,世界的运转也自有其规律,在失衡的天地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恒定,才是智者的态度。正如“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索尼娅:《我的沉默》这首诗似乎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沉默对您作为诗人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赵丽宏:沉默是什么?是无声,是哑口无言,还是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和能力?一个思想者,一个有情有欲有理想的人,不可能变成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没了声音,那意味着死亡。你说我的这首短短的诗“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谢谢你的理解!中国人有一句谚语:沉默是金。含义其实很复杂,它的意思并非简单地赞美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高洁的智者。当人声喧嚷,人人都争着发声、争着表态、争着表现自己的聪明或高尚的时候,你静默的姿态,你隐忍不发的态度,表达的是你的独立和正直,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不言不由衷。沉默的背后,其实有声音,这声音,也许振聋发聩。我的不少诗,其实是在沉默中写的,在赞美这种沉默的态度时,我的文字还是发出了声音,但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索尼娅:在《在天堂门口》这首诗中,您借助哲学人物探讨了存在问题。您如何看待哲学?哲学又如何影响您的诗歌?
赵丽宏:《在天堂门口》是这本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三百多行,集叙事、幻想、抒情和议论于一体。诗中出现了古今中外的哲人:老子、庄子、孔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屈原、但丁、尼采。他们相聚在天堂门口,却无法进入。因为,天堂门口藏着无形的斯芬克斯,这一群伟大的哲人,都无法回答来自天堂门内的提问。这是幻想的情境,是一个寓言,也是我对人类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一种看法。我在诗中和每一位哲人对话,但都是浮光掠影,无法真正进入他们的思想之海,无法窥清他们真实的灵魂。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睿智的思想者,他们一生都在追寻的道路上,没有一位能抵达终极的目标。他们的追寻和表达,营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哲学花园,引人入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幽深的花园里找到自己欣赏的花草,但没有一棵花草可以宣称:我就是美的终极,我就是真理的尽头。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者,一生的思索、创造和表达,其实都处在一个寻求的过程中,没有人可以抵达终极之点。无数这样寻求的过程,汇集成了浩瀚的智慧和文明的海洋,足以让芸芸众生在其中游览、观赏、沉思、感悟、惊叹。我想,哲学对我的诗歌的影响,在我的每一首诗中。
■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继续前行
索尼娅:在《母亲的书架》中,您提到了您的母亲。母亲这一形象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学和诗歌道路?
赵丽宏:我在诗中写到母亲,这是生活中真实的感受。母亲爱我,关心我,我曾经认为母亲不会关注我的创作,不会读我写的书,因为她从不主动说。多年前,当我发现,在母亲的卧室里,有一个她自制的书架,书架上放的,都是我写的书。这是世界上收藏我的书最完整的书架。对母亲的关爱,我无法用文字完整地表达。并不是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母爱,我有这样的母亲,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幸福。在我40岁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要第一个送给我的母亲。我不会在每一首诗中写到母亲,但母亲的关注和爱,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励,成为我写作的一种精神动力。《母亲的书架》是一首纪实的诗,这样的情景,人间稀罕,只需要用朴素的文字写出来,母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深情就饱含其中了。写这首诗时,我母亲98岁。今年1月,103岁的母亲与世长辞,我想念她!我会为母亲写一本书,不是诗集,但书中一定有我和母亲共同完成的诗篇。
索尼娅:本诗集以非常哲学性和沉思性的基调结束。您如何看待您未来诗歌的演变?您希望通过写作探索哪些新的领域?
赵丽宏:诗歌中有哲学,有思辨,有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和思考。但哲学家的结论,不应该出现在诗人的文字中。中国古代的诗人,也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中国的古诗,在唐代是一个高峰,唐诗的境界千姿百态,以风情神韵见长。到宋代,诗人追求以理入诗,曾被后人诟病。这样的争论,各执其词,其实并无胜者。诗歌和哲学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结合和关联,我在长诗《在天堂门口》有所表达,但也只能是一孔之见。未来的诗歌会有怎样的演变,我无法预言,我大概不会改弦更张,也不会标新立异,还会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继续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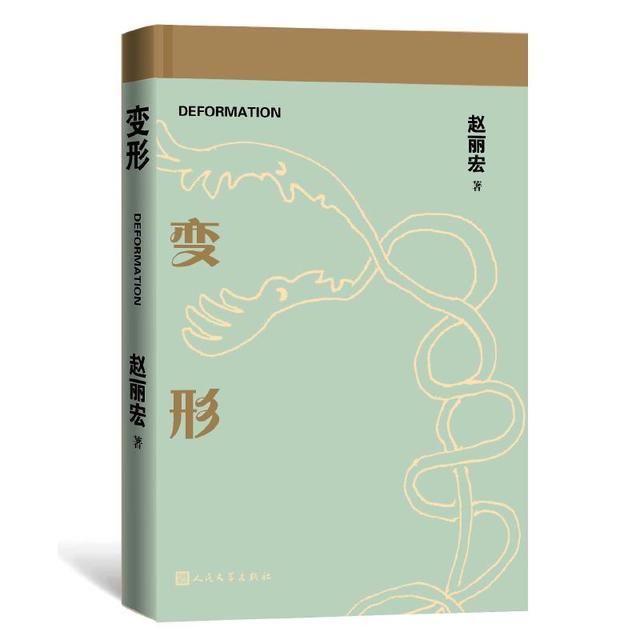
《变形》,赵丽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文字编辑:顾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