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先生与良渚

2001年7月,严文明考察桐乡新地里遗址,手捧刻纹黑陶豆。此照片后收入《考古学初阶》彩版,严文明自写文字说明,“良渚陶豆好大,刻划花纹好细”。

1977年秋,从左至右:吴绵吉、严文明和苏秉琦、吴汝祚等先生考察良渚遗址。
▌蒋卫东
4月14日深夜,惊闻严文明先生辞世,无尽的哀伤由心底升起,一夜辗转反侧。泰山其颓乎!哲人其萎乎!呜呼哀哉!随后几天,也想及时写篇怀念先生的文章,追思先生对于良渚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展示、申遗等工作苦心孤诣的贡献,但终究无法静下心来,那份无端揪心的哀痛,依然无计排解。于是,就重读先生关于良渚的系列论述,翻找先生在良渚的影像,先生与良渚的历历往事便断章式地浮现眼前,渐渐清晰。影像与文字,形成了超乎先生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
严文明先生是卓越的考古学家、考古学教育家,是中国当代史前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和引领者之一,他的学术人生,跟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主要的学术思想,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谱系、聚落考古、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环境考古、古史的考古学观察、大遗址保护等诸多方面,几乎都在跟良渚的“量子纠缠”中迸发出别样精彩的火花。良渚成为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阐发地。
2016年,先生在“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总结讲话中,将良渚遗址考古发现至今的八十年,分为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十年,从1936年施昕更发现发掘良渚遗址,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良渚文化,到随葬琮、璧、钺等重要玉礼器的草鞋山、寺墩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但“对整个文化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第二阶段二十年,始于1986和1987年连续发掘反山、瑶山两处高等级的贵族墓地,随后又连续发掘了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汇观山祭坛墓地、姚家墩聚落、塘山遗址、卞家山聚落等重要遗址,直到发现良渚古城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十年,始于2006年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不久,在古城东面约30公里处发现了一个以玉架山、横山和茅山等组成的遗址群,其中茅山发现了大面积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和配套的道路和水渠等,在古城西面发现了岗公岭等十处水坝与长达5公里的塘山共同构成古城外围庞大的水利系统。
先生长达71年的考古学术生涯中,十多次的良渚行迹和诸多关于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论述,跟良渚考古的三个阶段紧密呼应,可以将其对应地划分成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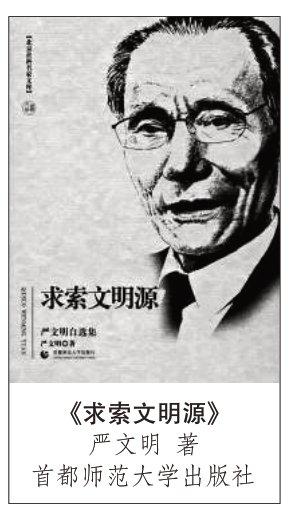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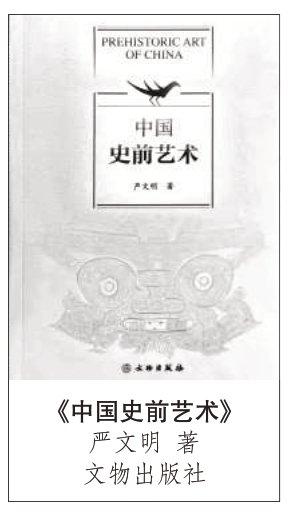
第一阶段,两次到访
第一个阶段,始于1958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的编写,结束于1986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前,为先生侧重于良渚文化谱系研究的阶段。代表性的论作有《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继1958年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时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得到夏鼐先生认可之后,1964年发表论文《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从浙江吴兴(湖州)邱城遗址1957年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着手,通过令人信服的缜密分析,前瞻性地指出“邱城下层、邱城墓地和良渚类型的遗存的顺序关系在本区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它们代表着本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此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本区新石器文化早、中期的文化命名,但本区存在着“以邱城下层为代表的早期文化遗存”、“以邱城墓地为代表的中期文化遗存”与“晚期——良渚文化遗存”的认识,在日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得到国内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环太湖地区最终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立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谱系。
这个阶段,先生只来过良渚两次。首次在1967年,借着“文革”中“大串联”的名义,先生独自跑到良渚镇,想看看良渚遗址的风貌。“因为时间短促,又没有专人指引,终于不得要领而回。但对于良渚附近的山山水水、肥沃的稻田、美丽的农舍,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一个人来去匆匆,先生首次良渚之行没有留下影像。
先生第二次到良渚,是时隔10年的1977年秋,在南京参加“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之后,先生跟他的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以及同行的考古学家吴汝祚先生,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的陪同下,前往良渚遗址考察,“先是在荀山一带看了几个地点,看了施昕更曾调查和试掘过的水塘,又看了几个曾出土玉器或良渚陶器的地方”,最后坐在大观山果园(1992年被改称为莫角山遗址)104国道边的一块草地上,一边休息一边聊天,苏秉琦忽然脑洞大开地说:“良渚是古杭州”。良渚博物院的同事夏勇在整理苏秉琦影像集时,发现了此次良渚之行的四张黑白照片,先生和苏秉琦、吴汝祚等的合影,为其中之一,拍摄地点当在良渚镇荀山一带——施昕更最早发现良渚遗址的区域,这是先生第一阶段良渚足迹的唯一影像。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早期,人到中年的严文明先生,厚积薄发,成果不断,迅速成为同龄考古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先生对姜寨遗址早期村落的初步分析,是国内最早采用聚落形态方法研究史前遗址与社会的经典。在对仰韶文化、黄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以及大汶口、青莲岗文化进行个案研究取得系列成就之后,先生开始整合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还在讨论国内各地龙山文化后,提出了后来被考古学界广泛接受的时代概念——龙山时代,指出龙山时代已经属于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这种聚落形态考古的方法论和统揽史前文化全局的概括能力及宏大视野,奠定了先生第二个阶段良渚研究的基调。

2009年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会场,严文明(站立者)与张忠培、单霁翔等先生交流。
第二阶段
文明起源说的良渚再探
第二个阶段,以1986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开端,结束于2006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后20年,是先生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研究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并关注良渚大遗址保护的阶段。
这个阶段先生精力充沛,硕果累累,陆续出版《仰韶文化研究》(1989年)、《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1997年)、《史前考古论集》(1998年)、《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年)等学术专著。关于良渚的专论有《良渚随笔》、《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八篇,而在这一时期先生的其他多篇代表性论著中,如《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长江文明的曙光》等,也都较大篇幅地涉及到良渚文化或良渚遗址的研究。
文明起源是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先生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说和满天星斗说的基础上,按照文化演变发展的谱系关系,将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划分为12个文化区,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的文明起源模式。“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圈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性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是中华民族特别强固的凝聚力所产生的根源”。“重瓣花朵式多元一体结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积极探索,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与境界。

1998年,发掘桐乡普安桥遗址临近收尾,严文明在考古队宿舍唱卡拉OK。
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是先生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观察和阐发对象,内容涉及环境与生业、资源与社会、技术与文明、信仰与艺术等方方面面,从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时代“走在前列”,到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的文明社会”。既强调“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也“把良渚文化看成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对良渚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先生通过聚落遗址的等级和埋藏制度等方面来分析、研究良渚社会的性质及其文明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机械比对所谓文明标准或文明要素的方法。
先生还是稻作农业起源“边缘理论”和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说的提出者,向来重视稻作农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屡次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最早实现了犁耕,石犁的使用,以及破土器、“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稻作农具的出现,提高了耕作等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给良渚社会提供了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才能使玉器、漆器、丝绸乃至陶器等手工业获得全面的发展,促使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这是良渚文明产生的必要前提。
中国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在这个阶段取得骄人成果,先生对此高度敏感和重视,又提出“城址的出现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并诗意地表达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都城是国家物化形式的集中表现,是各种文明因素的总汇。”
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城址时,先生就多次强调,良渚遗址是“一个有规划的产物,不是自然生长的结果”,将良渚遗址看做一个精心规划、有着明确功能分区的统一整体,甚至敢为人先,多次前瞻性地推断良渚遗址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或“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台城”,“当然并不排除在它的外围还会有其他的防卫设施。”
受先生启示,1998年11月下旬,我在良渚遗址西部区域踏勘时发现多条长垄状土墩,撰文认为它们应是良渚时期古城址的城墙遗存,从而提出“良渚遗址群范围内,至少包含有两种不同形态、不同等级的聚落类型——西部的城和东部的村落”。先生和我的探索,在良渚古城发现后都得到了验证。
这个阶段,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的先生,来往良渚的频次远远超过了前一个阶段。除了没能找到1986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相关影像,先生其他几次良渚之行大都留有影像。先生所著《长江文明的曙光》(增订版)彩版第一页,收录两张照片,文字说明分别是“1987年12月2日我与李水城在牟永抗和王明达等陪同下到莫角山考察”、“1992年12月26日在杨楠陪同下冒雨考察莫角山宫殿基址上的夯层遗迹。”1992年杨楠主持发掘莫角山遗址,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先生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前来检查发掘现场并指导工作,12月26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良渚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在牟永抗和王明达等先生率领下几乎全员出动,不仅在雨中留下了一张近乎全家福的照片,而且也在现场聆听了先生对于莫角山夯土基址重要性的解读和下一步发掘工作的建议。1995至1998年,北京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三方联合发掘普安桥遗址,先生担任中方总领队,留有多张影像,其中一张,记录下1998年考古发掘临近收尾,先生在考古队宿舍全神贯注引吭高唱卡拉OK的情景,显示了先生工作时扎实、严谨、不苟言笑,工作之余乐观、多艺、热爱生活的另一面。2001年7月,先生到我担任考古发掘领队的桐乡新地里遗址指导,拍下一张手捧刻纹黑陶豆的彩照,收入《考古学初阶》一书的彩版,先生自写了文字说明,“良渚陶豆好大,刻画花纹好细”。此外,2002年6月8日,先生和张忠培先生联袂考察良渚塘山遗址,上手观摩制玉作坊出土的废弃玉料和制玉工具,2006年11月,先生参加“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也都留有珍贵影像。
就在良渚遗址因一次次重大考古新发现而风光无限之际,遗址保护却迎来了最艰辛困难的挑战,乡镇规模膨胀、办厂开矿、沿路开店、违章建筑、盗挖盗掘,形势严峻,尤其遗址北侧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有30多家,“山上挖开了一个个的口子,天天放炮,轰隆轰隆巨响,拉石头的拖拉机马达声像坦克似的,碎石机的声音又像机关枪,烟雾弥漫,简直就是一个大战场。”“如何保护好良渚遗址,现在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迫切而又困难的任务”,出于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先生开始坚持不懈地为良渚遗址保护奔走疾呼。
当二十一世纪良渚遗址保护迎来全新篇章之时,先生又不遗余力地支持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工作。2002年9月,先生应浙江省政府之聘,成为浙江省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咨询委员。2006年11月,先生在“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讲话时,继续强调“要加强遗址的调查勘探和保护”在先生等专家的奔走呼吁和国家、省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新世纪初,良渚遗址保护开始建立长效的机制体制,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和政策保障,逐渐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

2016年11月,严文明考察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与王宁远、赵晔、陈明辉等中心年轻考古学家们合影。
第三阶段,晚年学术的自我革命
第三个阶段,自2006年良渚古城发现至先生辞世,为先生全面总结良渚文化研究成果和大力推进良渚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阶段。虽然年事渐高,但先生晚年在学术上依然孜孜以求、“勤于耕作”,有《中华文明的始原》(2011年)、《足迹:考古随感录》(2011年)、《中国新石器时代》(2017年)、《考古学初阶》(2018年)、《丹霞集——考古学拾零》(2019年)、《中国史前艺术》(2022年)等新著和文集出版。关于良渚的论述也有《良渚古国,文明奇葩》等多篇,这些论述都凝练了先生对于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价值认识的总结,寄托着先生对于良渚遗址考古和保护工作再上台阶的殷殷期望。
对于“如此发达的良渚文化,到底是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是不是建立了国家”,先生做出了深思熟虑的答复:良渚社会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分化,有贵族和平民,有高等贵族和普通贵族,同时还有职业分工,显然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良渚时期明显建立了国家,而且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良渚古国应该是中华文明开创时期的一朵奇葩。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良渚文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与此同时,先生还为良渚文化划了四个呈层圈外延的“区”:以古城为标志的核心区,环太湖的主体区,北至苏北、西至赣皖、南至浙南的扩张区,以及范围波及山东大汶口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陕西石峁等的影响区,“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给广大地区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他还做了七言长诗《良渚颂》,以澎湃浪漫的激情、丰富绚丽的想象力,全面讴歌了良渚文化高度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及其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
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对于史前艺术的综合研究,向来是欠缺的,先生却以九十岁高龄出版《中国史前艺术》专著,按照各地不同风格,将史前艺术区分为三大系统(与罐文化、鬲文化和鼎文化三个系统密切相关)和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转型期四个时期,并作了简约概要式的归纳。这种于晚年走出自己熟悉园地、探索陌生领域的勇气,与一般老人易固易我的常态,形成鲜明对照。
耄耋之年的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探讨玉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有很多特色,玉文化是其特色之一。研究古代文明通常包含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玉文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重要的表现。”因而在这一阶段的良渚文化和史前艺术研究中,先生都特别强调,“玉器的使用已经渗透到良渚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良渚古国文明的集中表现。”甚至还接受了曾经并不认可的“玉器时代”,“良渚时期……如果强调玉器的作用而划为玉器时代也未尝不可。”这对于“龙山时代”提出者的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番学术的自我革命,而这种自我革命尤能体现先生的学术境界和人格魅力,尊重考古发现的真实性,宽容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大气开放,勇于探索,不唯我独尊、固执己见,毕竟在学术的原野上,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这个阶段,随着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独特价值更加凸显,相应地,先生对良渚遗址考古和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8年,先生参加“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对良渚古城考古规划提出了多学科合作、多角度和全方位研究的要求。次年,先生参加“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提出“大遗址的保护一定要与考古工作相结合,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可能逐步发现、逐渐认识,很难一步到位。因此做规划时一定要留有余地”“把遗址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建设遗址公园……考古就得先行,考古工作跟不上,就不能轻举妄动”等要求。在这个阶段,先生对良渚博物院的展览陈列策划文本、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遗文本,也都给予过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
在2012年八十周岁之前,先生频繁来良渚现场指导,留下了不少影像: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先生不顾75岁高龄,飞赴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指导,指出良渚古城的发现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并欣然题词“良渚古城,文明圣地”。2009年,先生参加“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对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又作了三个方面特别的强调。2016年11月,先生来杭州参加“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先生考察了老虎岭水坝遗址和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留下了在良渚足迹的最后一批影像。
这些影像和文字,业已成为先生与良渚的重要文献和遗产。当我们凝视这些带有明显写实性的影像,重温充满想象力的文字时,我们感受到了先生对于良渚念兹在兹的深情。先生关于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一系列论述文字,是先生学术思想的缩影,体系全面、纵深、完整,无疑已凝固升华成为先生学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和状态。在先生良渚之行的影像中,我们眼看着先生慢慢变老,形容慢慢枯槁,面目慢慢憔悴,精神却不妥协地依旧矍铄,目光也不妥协地依旧坚定。
(本文作者为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