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评《难民帝国》︱作为历史线索的北高加索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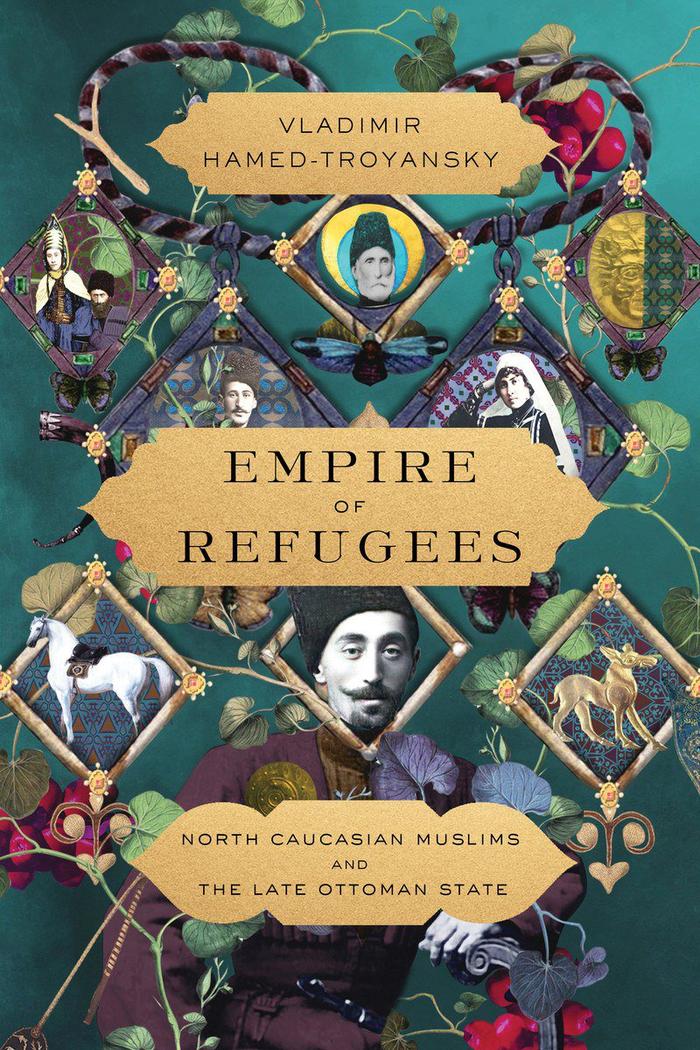
2022年4月,在土耳其海峡大学(BoğaziçiÜniversitesi)访学的笔者刚刚收到自己的土耳其暂住证(ikamet),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笔者决定在当地的银行开办账户。笔者首先来到附近的某家私人银行的分行,然而当笔者用土耳其语请求工作人员的帮助时,工作人员用支支吾吾的英语告诉笔者,近年来土耳其难民问题严重,因此土耳其政府加强了对外国人银行账户的管控,现在只有少数银行还办理外国人银行账户的业务,她建议笔者去隔壁的农业银行(ZiraatBankası)开户。笔者当天就成功在农业银行开办了账户,但是这只是战争难民影响笔者在土生活的开始,再后来,店铺里的俄语广告越来越多,老牌购物中心珍宝(Cevahir)商场里的电器城开始使用土俄双语标识,伊斯坦布尔大学附近的一家移民中介甚至只用俄语做广告。土耳其政府也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管控,根据内政部的新规定,如果一个街区(mahalle)的外国人占街区人口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那么新搬入街区的外国人无法获得暂住证,这导致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朋友因为暂住证问题无法搬入笔者所在的共和(Cumhuriyet)街区。笔者这才意识到难民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事实上,这不是难民问题第一次对中东产生巨大影响。早在一百多年前,来自北高加索的穆斯林难民(muhacir)就给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UCSantaBarbara)大学全球研究系(DepartmentofGlobalStudies)助理教授弗拉基米尔·哈梅德-托洛扬斯基(VladimirHamed-Troyansky)博士的新书《难民帝国:北高加索穆斯林和晚期奥斯曼国家》(EmpireofRefugees:NorthCaucasianMuslimsandtheLateOttomanState)就讲述了这段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历史。作者在导论部分明确表示,本书的研究问题是,来自北高加索的穆斯林难民如何改变晚期奥斯曼帝国,以及晚期奥斯曼帝国如何解决难民安置问题(VladimirHamed-Troyansky,EmpireofRefugees:NorthCaucasianMuslimsandtheLateOttomanState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24,2)。自1860年奥斯曼帝国成立专门的难民安置机构——难民委员会(MuhacirinKomisyonu),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在这段时期奥斯曼政府安置了约三百五十万难民。这些难民加速了奥斯曼统治在巴尔干的崩溃,但也强化了帝国在黎凡特(东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统治。作者随后解释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muhacir,这个词在历史上被用来指代穆斯林难民,另一个是“切尔克斯”(Circassian),切尔克斯是北高加索众多民族中的一个,但在历史上这个词被用来指代所有北高加索的穆斯林。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北高加索的史地。
本书正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了正文前两章。作者在第一章介绍了俄国在北高加索扩张的历史,作为北高加索穆斯林难民问题的背景。俄国的种族清洗和镇压反抗过程中使用的焦土政策是难民问题爆发的重要背景,俄国在北高加索废除奴隶制,也导致一些奴隶主逃往奥斯曼帝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大约有七十万到一百二十万高加索难民逃亡。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沙俄政府一度禁止穆斯林移民他国,并禁止移民到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回国,这与奥斯曼帝国对移居俄国的亚美尼亚人的限制形成了平行关系。作者在第二章介绍了奥斯曼帝国对难民的管控。作者指出,难民管理体系的法律基础是1857年的《难民法》(MuhacirinKanunnamesi)和1858年的《土地法》(AraziKanunnamesi),主要执行机构是难民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让难民离开城市,在乡村定居。奥斯曼政府管理难民的基础是一种信念: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穆斯林主导的国家,有义务保护来投奔的穆斯林难民。为了做好难民安置工作,奥斯曼政府对北高加索穆斯林难民的身份和技能进行登记,丈量土地以提供安置用地,限制已安置难民的再流动,并且有时候刻意把难民安置在游牧部落生活的区域。通过这些手段,帝国政府获取了对国土的知识,并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第二部分包括了全书的第三、四、五章,作者研究了三个难民安置的案例:巴尔干、(外)约旦、安纳托利亚(锡瓦斯Sivas)。在第一次高加索难民危机(1863-1865年)期间,有大约五十万北高加索穆斯林难民被奥斯曼政府安置在巴尔干。政府有意把难民群体打散,安置在小型村落里,在难民安置的区域,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委员会成为了难民和政府之间的纽带。然而这些难民的到来让有限的土地变得更加紧张,激化了当地的族群矛盾。在(外)约旦,奥斯曼政府把难民安置在游牧部落和城镇之间的区域,政府允许难民选择定居点,难民建立了安曼以及其他一些城镇,希贾兹(Hejaz)铁路的开通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事实上今天约旦的前四大城市里有三个是北高加索难民建立的。在安纳托利亚,通过对胡塔特(Khutat)家族的案例研究,作者探究了难民在锡瓦斯的长台(Uzunyayla)地区定居的历史。1859年后,大量北高加索穆斯林难民涌入,来自北高加索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难民在长台地区建立了各自的定居点,之后建立起长台地区的中心城镇阿齐兹耶(Aziziye)。因为长台地区交通不便,定居在这里的难民成功保留了许多北高加索的文化传统。总的来说,巴尔干的难民安置动摇了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而锡瓦斯和(外)约旦的难民安置则巩固了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
第三部分包含了全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主要研究这些难民形成离散群体(diaspora)的过程。北高加索难民一方面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习俗,另一方面也建立了新的社区和组织,比如1908年成立的切尔克斯团结互助会(ÇerkesİttihadveTeavünCemiyeti)。对于他们来说,矛盾的核心在于,北高加索是一个内部多元的地区,但是他们需要建构一个统一的北高加索身份。总的来说,这些难民中的精英宣传对高加索故土的热爱和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强调难民付出的牺牲,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其中一些人还参与建立了现今土耳其足球三大豪门之一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不过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政权禁止了所有北高加索组织,直到195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后,北高加索难民的组织才重新开始活动。而一些对新生活不满意的难民试图回归俄国,但俄国一度禁止难民回国,1865年车臣难民的集体回国的企图和1880年阿布哈兹难民回国的尝试导致两次难民危机。不过难民成功建立了一套偷渡回国的网络。在1867年后,尽管俄国在官方层面上维持对难民归国的禁令,但是会通过个人提出的回国申请。在回国后,这些难民不能回到原籍,他们会被安置到其他地方。作者总结,无论奥斯曼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难民强化国家,两个国家的难民政策都有连续性,但是也保留了协商空间。作者在全书的最后简单介绍了现当代北高加索海外群体的活动。
本书在今年二月出版后,迅速引发了学术界的反响。作者哈梅德-托洛扬斯基博士被邀请到多家著名学术机构进行演讲,也包括笔者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对于出版第一本书的青年教师来说,这类经历并不是多见的。那么为何本书能迅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首先得益于作者之前的经历。哈梅德-托洛扬斯基博士在出版本书之前,已经是学术新星,他在《国际中东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ernStudies)等顶级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论文,并获得了多个奖项,是一位备受关注的青年学者。当然,本书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还是本书的质量,笔者认为,这是可能是近年来英语学界关于奥斯曼历史的著作里最优秀的一本。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工作,本书的史料工作让人惊叹。哈梅德-托洛扬斯基博士在三大洲的接近十个国家里收集了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言书写的历史资料,既有土耳其、约旦、英国、俄罗斯等国的国家档案馆里找到的政府资料,也有北高加索的难民后代提供的私人信件等民间史料。作者强大的语言能力使得他能够收集和阅读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多维度的研究,既涉及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上层的制度设计,也涉及这些难民的生活。在当今的学界,像作者这样有能力在多个大洲用多种语言开展研究,特别是使用俄语和阿拉伯语这两门史料丰富但是难度颇高的语言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
在扎实史料工作的基础上,本书用难民作为线索,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多个地区的历史串在一起,也把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一位学者很难兼顾多个方面,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地域广大,内部差异巨大的国家,因此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碎片化倾向,一个研究奥斯曼时期埃及经济史的学者和一个研究巴尔干地区政治史的学者可能存在隔阂,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研究,也并不熟悉对方领域的经典作品。然而哈梅德-特罗扬斯基博士通过对难民的研究,把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历史结合在了一起。本书第二部分对难民在高加索、(外)约旦和锡瓦斯的研究,就成功地把不同的地区放在难民安置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到对外约旦这一章节,作者对被安置的难民和当地的游牧部落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分析,于是把难民和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一大问题:部落,结合到了一起,在这一章里作者又研究了难民定居点和当代约旦主要城镇之间的继承关系,指出约旦首都安曼的商业区巴亚德尔(Bayader)区正是在难民的定居点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成功的城市史和经济史的案例研究。本书通过难民将多个问题、多个区域串在一起,并展示了难民对这些区域带来的长期影响:巴尔干的族群冲突;部落的定居;锡瓦斯和安纳托利亚的开发;约旦首都安曼的建立和兴起,等等。作者提及的多个问题在未来都可能是某篇博士论文进一步研究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将为未来的许多研究打开大门。
而在多个区域之间,作者对安纳托利亚,特别是奥斯曼-俄国边界地区的历史的研究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二十年前,奥斯曼历史研究专家苏莱娅·法洛齐(SuraiyaFaroqhi)就指出,“能够阅读俄语,熟悉俄国历史,这是任何国家的奥斯曼历史研究者中都少有人能做到的事”(SuraiyaFaroqhi,ApproachingOttomanHistory:AnIntroductiontotheSources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186)。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以及现当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和苏联/俄罗斯之间发生过紧密的联系,既有战争和冲突,也有和平的合作和交流,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土耳其的活跃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段历史的延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两国之间关系史和两国边境地区的历史的优秀作品并不算多(至少在英语学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奥斯曼土耳其语和俄语都是学习难度颇高的语言(学者甚至还需要学习高加索当地的语言),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学术体制把两个国家分割在了近东/中东研究和东欧/斯拉夫研究两个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两国档案馆的开放程度有限,等等。近年来,有更多的学者开始书写关于奥斯曼-俄国的交流,以及两国的边界地区,即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的历史,例如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Reynolds)研究了一战中的高加索战场,以及战争结束后现代高加索边界的形成(MichaelA.Reynolds,ShatteringEmpires:TheClashandCollapseoftheOttomanandRussianEmpires,1908-1918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霍莉·希斯雷尔(HollyShissler)和詹姆斯·迈耶(JamesMeyer)则关注从艾哈迈德·阿迦奥卢(AhmedAğaoğlu)等从俄国统治下的高加索来到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偏重个案研究(A.HollyShissler,BetweenTwoEmpires:AhmetAğaoğluandtheNewTurkey London&NewYork:I.B.Tauris,2003 ;JamesH.Meyer,TurksAcrossEmpires:MarketingMuslimIdentityintheRussian-OttomanBorderlands,1856-1914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 ),格兹德·久吕特(GözdeCörüt)详细研究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双重国籍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奥斯曼-俄国边境的管控政策(GözdeYazıcıCörüt,LoyaltyandCitizenship:OttomanPerspectivesonItsRussianBorderRegion,1878-1914 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Unipress,2021)。这些自然都是填补知识空白的优秀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大多都局限在两国政府政策制定的上层视角,抑或是跨境知识分子等精英人物,而《难民帝国》一书通过对口述史、私人信件等私人史料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不同的世界,让我们了解到具体的某个难民或某个难民家族艰难求生的故事,给我们谱写了一首北高加索难民的史诗。本书为奥斯曼-俄国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视角,让读者能看到大历史背后那些鲜活的人,笔者认为这是本书的最大贡献。
总的来说,本书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工作之上,以北高加索难民作为线索,书写了一部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人群的历史,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学著作。考虑到土耳其和中东其他国家当前被新的难民潮所困扰,笔者认为学术圈之外的读者也可以考虑阅读此书,了解曾经的难民潮对中东造成了哪些深远的影响,以史为镜。最后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作者弗拉基米尔·哈梅德-托洛扬斯基博士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在《难民帝国》一书的结尾,他感谢了这些历史上的北高加索难民,以及难民的后人,为他提供了研究的材料,接着他一一列举了本书提到的难民的结局。钱穆先生曾提出,“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想必哈梅德-托洛扬斯基博士对他研究的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中具体的人,就抱有钱穆先生所说的这种“温情与敬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