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被焦虑、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
谈论他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消费的名字,一种能寄托许多情感的象征物,也是最常见的、很能显示作者阅历的缅怀卡夫卡的方式。
卡夫卡在100年前的6月3日离开这个世界。到今天,谈论卡夫卡的生平而不涉及其作品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也如此。他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他个人书信、日记里流露的情绪困境,都越来越明显可感了;而就我所见谈卡夫卡的文章,要么继续在讲他作品中对今日社会的恐怖的预见性,要么尽可能把他“还原”成为一个被焦虑、恐惧、犹豫、不自信所缠绕的“有血有肉”的人。
卡夫卡是一个文化符号,这毫无疑问,因此谈论他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消费的名字,一种能寄托许多情感的象征物,也是最常见的、很能显示作者阅历的缅怀卡夫卡的方式。

跟别人也跟自己论辩
一个戴礼帽的男人,拎着根手杖,走进一家餐馆坐下。男人从帽檐下扫视着周围。餐厅很大,四周站着、走着不少服务员,没有一个人注意他,更没有人走近他,问他要什么。他的心中开始冒出一连串不忿的问号。
“为什么他们不理会我?他们是不是看我是外国人?”他想着,“每个服务员都是健全的,手里都有托盘,他们就让我一个人干坐着?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男人想着,看着,却不挪身子。直到另一个顾客从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嗨,这是一家自助餐厅,您只需要去取餐就可以了。”
看了这段故事你会想到什么?会不会觉得这男人很夸张,想得太多,太以自我为中心,太善于给自己“加戏”?抑或他脑子里从没有考虑过“国情”之类的东西?叙事的人是I.B.辛格,他是一名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在二战前的1935年移民美国,以写小说为志业。日后在一次访谈里他讲了这件事,像是自嘲,然而他接下去的评论和反思更加“夸张”,他说:
“我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解释。但即使我在那里坐了100万年,我也不会想到这可能是一个自助餐厅。我把这比作那些对万能的上帝提出问题的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
作为一个感觉受了怠慢的顾客,他坐在那里跟自己论辩。他在尝试用各种方法理解现状,不断地向自己提问,也向神灵提问。他根本没有疑心自己是否走错了地方或来错了时间,也没有考虑过“文化差异”“国情”等半分。他似乎是这么想的:这个地方不符合一家餐馆的定义,那么我怎么把它合理地解释为餐馆?
继续研究辛格的思维,也许会深入让人望而却步的哲学。我还是继续用设身处地的方式来讲述后续:假若是我自己第一次在异国的花花世界认识了自助餐厅这种东西,我会怎么向一个跟我对话的人总结这个故事呢?我可能会说:看,当年的我多可笑,多不识世面!我可能会说:其实自助餐厅很贵,根本不合算;我可能会说:附近有一家什么什么餐厅不错,推荐给你……
但辛格对这件事的总结继续出人意料。他强调的是,自己获得了一种认知:
“现在我有时候会去自助餐厅,但是最起码,我懂了,我完全了解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事了。(Ihavelearned.Iknowexactlywhathappens.)”
“我懂了”“我会了”“我了解了”,仿佛这一点点明白,就给他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成就感。从不知到认知,在他这里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他既敏又钝,既老成又天真。他从与一个场景的相遇时刻开始回忆,然后用论辩的方式去重述它。在重述时,往事一下子出现在了当下。
在辛格的写作中游荡着卡夫卡的魂灵。相遇时的惊讶,然后是不住地提问。上帝并不存在,于是那个人问个没完,他不会撤回自己的前提——不会取消这次相遇,或是跟自己说“我不该来”“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当阻碍发生,他宁可观察后续,也不会怀疑自己之前的做法都是错的。此时当然可以联想到卡夫卡那个著名的短篇:《在法的门前》。
“在法的门前站着一名卫士。一天来了个乡下人,请求卫士放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卫士回答说,他现在不能允许他这样做。乡下人考虑了一下又问:他等一等是否可以进去呢?”
卫士说有可能行,但现在不行。由于法的大门一直开着,乡下人就弯着腰往门里瞧。卫士发现了,笑着说:“要是你很想试试,就不妨进去,把我的禁止当耳旁风好了。不过得记住:我可是很厉害的。”听了他的话,乡下人没有进去。“他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家可都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以进啊……”他去观察卫士的面容,鼻子和胡须,然后坐在卫士给他的矮凳上,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傻傻地请求,但是始终没有进去。
乡下人没有别的事可做吗?他想进这道门的理由是“听说所有人都向往法律”,可他所做的实际上是与卫士一轮轮地费口舌。从这个故事自然就会想到《城堡》,故事里的土地测量员K也是明知自己有可能是错派来的,却从第一天抵达开始,他就自始至终地谋求进入城堡。可是K为什么放着他“明知”的事情不管,一味地往前呢?真正进去城堡了,他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还是就为了获得一种“认知”:他来这里究竟是什么意义?
杠精作为一种存在方式
但无数的感知都朝那些消极的字眼会聚,《在法的门前》,还有像是《在流放地》《判决》这类卡夫卡的名篇,人们总免不了从“寓言”的角度去谈论,既是寓言,它就可以夸张,可以不符合现实逻辑,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讽刺,要影射,要迂回地批判某种现实中的东西。但就像卡夫卡作品最早的评论者瓦尔特·本雅明所说,他并不能确定,卡夫卡到底希望人们怎么读他的小说:是考虑它的寓言色彩,还是纯从表面?
纯从“表面”来读他的故事,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人物有深度的提问癖,借助提问,他们活在每一刻的当下,似乎话语使他们无所不在,兴致勃勃,即便走投无路也能说会道。就以《城堡》为例,它的阴暗诡异被无数次讲过了,作为主人公的K本质上是个不幸的人,这也是共识。但像《城堡》这样的故事是不能简单地勒上一根共识的腰带的。它的开头说:K在一个雪夜抵达了一个村庄,进一家酒店找过夜的地方,店老板没有地方出租,但他对K的到来感到“极度惊讶和慌乱”,就愿意让他在店堂里一个稻草口袋上睡觉。K“也同意这一安排”。他躺倒了睡去。周围有几个农民在交谈。
卡夫卡热衷选择传达的信息,往往出其不意。店老板为何“极度惊讶和慌乱”?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叫醒了K,他长着“演员似的面孔,浓眉细眼”,这种外貌描写同样突如其来。周围那几个农民也凑近来听了。年轻人跟K说:自己是城堡主事的儿子,城堡则是伯爵大人的,在村里过夜的人算是在伯爵大人的领地上过夜,必须有伯爵的许可。
K闻言半坐起身子。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先质疑对方话里的前提:“这里是有一座城堡吗?”
他也许是装糊涂,但装糊涂所需要的老到,似乎并不是他这样的。在卡夫卡的引导下,我们退后去看这个对话的场景。年轻人回答:“那还用问?”然后,周围的其他人也大惑不解地冲K摇头,并说“这里是伯爵大人韦斯特威斯的城堡”。
这时K才问“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过夜吗”,给出肯定的回答后,年轻人朝周围的人“张开双臂”,寻求共鸣。戏剧性的场景持续发生,他说:“难道竟有什么人可以不必得到许可吗?”卡夫卡补充了一句,说他的话音里带有强烈的嘲笑。而K呢?他打着哈欠说:“那么我只好现在去讨要许可了。”
问谁讨要?当然是问伯爵。这话激怒了年轻人:深更半夜去问伯爵要许可证?K神色泰然地回答:“这不行吗?那你为什么叫醒我?”
在一连串的质疑和反问之下,K把他和面前的对手,以及整个酒店的空间都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那个年轻人接下来的反应可谓是正常的:“真是个死皮赖脸的流浪汉做派!”之后,K才一边躺回被子里去,一边用“异常轻的声音”说出了他的泰然自若的缘由:他是伯爵聘来的,他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第二天,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器具过来。
原来K是“有来头”的人。但这种交底并没有使相遇的一幕就此变得无聊,也没有把接下来的故事变成占优的一方对唯唯诺诺的另一方的一面倒的欺凌。K是一个有论辩癖的人,接下来的几天里,K在村中认识各种人,有一位教师带着一群孩子,打了招呼后,教师问:“您不喜欢这城堡吗?”
教师的反问,激起了K的回问:“为什么您要猜想我不喜欢它呢?”等教师回答后,K继续问“您认识伯爵吗?”教师红着脸走开:“不认识。”K继续反问:“您不认识伯爵?”教师也以反问反诘:“我怎么会认识他?”然后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解释了自己不便于再回答下去:“请您考虑一下有这么多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旁边。”
如果非要对K做什么涉及道德的评价,那么,哪怕只读了《城堡》的一章或半章,也能看出他是个善于并乐于反复纠缠的人,有时他简直像是杠精,可每句话又杠得不无道理。在每一次相遇中,K都能用话语缠绕住对方,同时还常常做得仿佛是自己被对方所打扰一样。那些话语常常不像要达到什么具体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说而说,为了问而问,为解释而解释,为了把话继续下去,他各种提问,无限地解释。
即便当事人拂袖走脱,K的话语也不会停止,而是转入大脑之中继续进行。《庄子》中有一句名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实际上,每一句话,只要你能抓住对方话中的一点发问,这话也可以像“一尺之棰”那样,被无限地切分下去——《城堡》里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有时候,卡夫卡小说传达的疲惫感和徒劳感,不像是在讽刺或批判什么,倒像是人物的一种存在方式。
电话那头有没有上帝?
一个人如此唇舌流利,不屈不挠,却教人看不出他想要得到什么。这是卡夫卡小说里最陌异的地方之一。假如从疲惫、徒劳、无助的角度上认同那些小说,认同《在法的门前》里的乡下人,认同《城堡》里的K,固然可行,但并非唯一之途。通过堆积话语来“刷存在感”,往深里说,是源于神学上的感受力:唯一的上帝不仅存在,而且永远不会现身回答,于是人就不停地问、不断地呼喊,就如同持续地拨打一个无人接听的电话,以此来确信电话那头是有人的,只是故意不讲话。
K那种类似“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那种“死皮赖脸”的做派,是戏剧性的,它违背我们的常识,可是符合他自己的逻辑。当我们平时碰壁,做事受阻,我们常见的反应是“我不该来”“我不该做这件事”,还会劝告别人说要“及时止损”;可是,如果你这样劝说一个K这样的人,或是卡夫卡这样的人,他会怎么回答?
他会反诘:“我不该来?这事我不该做?那我干脆别出生好了。”
我既然来了,既然在了,我就要继续前进,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也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会去认知,会去解释。卡夫卡的生平和性格,如今被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但我不热衷于对他的“正确”理解,我更关心的是,在这种日渐学术性的趋势发生之前,人们如何传说他的故事,如何谈论他,借他说事。
1968年12月20日,马克斯·布罗德逝世,他就是保管了卡夫卡的档案手稿又背叛了卡夫卡遗嘱的人:他没有把包括《城堡》在内的长短篇小说烧毁,而是将其发表。当年他拖家带口逃脱纳粹追捕的故事,本身也足以写成一部精彩的传记,难以想象,如果布罗德当时和《城堡》等书稿一起落到纳粹手里,今日还有没有人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并成为他的信徒、读者和朋友。
一年半之后的1970年,年近七旬的I.B.辛格,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卡夫卡的朋友》,在书中那篇同名小故事里,辛格写了一个曾与卡夫卡有密切往来的人物。此人(名叫雅克·科恩)亦是个滔滔不绝之徒,他说自己是1911年在布拉格的一次戏剧演出上,在后台第一次见到卡夫卡的。“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一个天才站在我的面前。我可以闻出来,就像猫闻见老鼠。”
他说话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一样有种怪诞的夸张感。他喜欢谈论自己和女人的关系,他曾说,某夜某个光脚的年轻女人,半夜里来敲他的门,要他救她,“我只需要在你屋里待到天亮”,科恩放她进来,为了谁睡在哪里争论了很久,“最后决定一起躺下”。到了半夜,女人的情人砰砰砰砸门,“我惊诧门居然扛住了……我极度惊恐,但是心里某个地方不住地发笑”。情人走了,过了几天,“奇怪的是,那个男人那晚就消失了”。
他戏剧性地讲完这些,紧接着谈起卡夫卡:“卡夫卡,虽然他年轻,但困扰我这老头的那种拘束感也支配着他。在样样事情上都妨碍他,性、写作。他渴望爱,逃离爱。他写下一个句子,立刻涂掉。”他谈起某日强拉着卡夫卡逛妓院,在走上歪歪扭扭的小楼梯,拉开门,一众女人出现在面前时,“卡夫卡颤抖起来,拽我的袖子。然后他掉头,飞快地奔下楼梯,我担心他摔断腿。一到街上,他就停下来,如小男生般呕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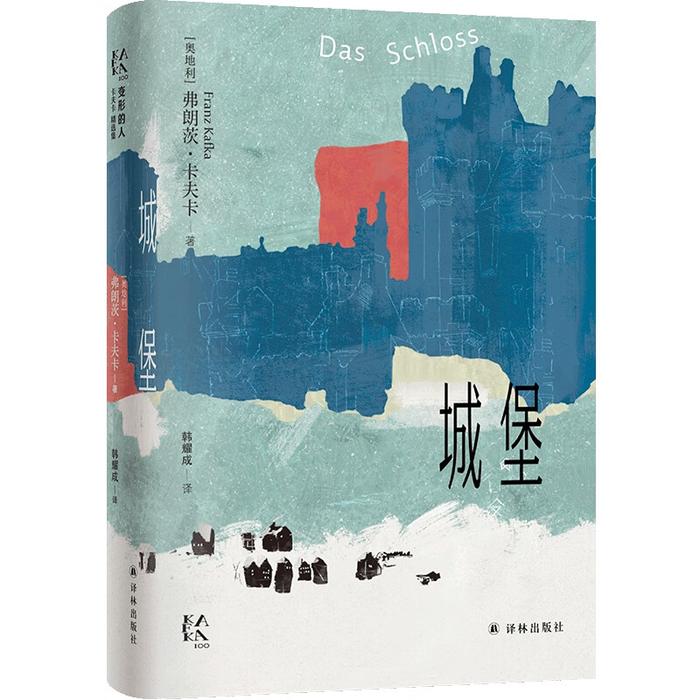
《城堡》
[奥]弗朗茨·卡夫卡著
译林出版社2024年5月版
